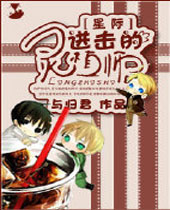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开的一只手在致意。教皇非常熟悉他们,他让他们激动不已。他坐在他的教皇车上,穿行在正好是那巨兽的肚皮上,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仿佛是一场电击那样。从远处你看不见他,但是你看得见那升起的热情浪潮就像白色和黄色的人浪。舞台也是白色和黄色的,不漂亮但显得庄严,就在那上面做弥撒和为六百年前的波兰女王贝阿塔·埃得维戈封圣的仪式。在那上面,疲倦的教皇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弯着腰,要做加冕礼那样的极为繁琐的仪式,但是他能够发出有力的声音。在那种时刻并不害怕掌握着一百万人,要对他们说:祝你幸福,母亲波兰。他几乎被其宝座所吞食。在他周围,像展示在橱窗里的神职人员显示出一个胜利教会的图景,这并非总是容易消化的。你看那《福音书》,用大块黄金装帧,像偶像一样,以高举过头的手抬着,作为一面神圣的旗帜向人民展示。用不着是完全世俗者来感觉到一种害怕的余味,当最后他们把它放下并简单地就是宣读它的时候,才让人松了一口气。
不叫人害怕的是那平静的巨兽一百万人。它使你感到吃惊,这是真的。这有点儿是一个谜。谁要是想那些人是老太太、怀旧者、牧师和修女,那他就没有明白:在那里有数十万年轻人,就是喜欢耐克、迈克尔·杰克逊、电子游戏机和口袋里装着避孕套的那些年轻人。而你在那里看到,在举扬圣体时,他们全都跪下,在疲倦的教皇面前低着头。教皇说了非常漂亮的事情(必须学会和保护自由的快乐),并要求似乎不尊重时间和对人的温柔的一种正教。他们拿着他们的白黄色小旗,怀着纯朴而简单的信仰,他们心里想着怎样的未来呢?天堂,他们怎样想像它呢?我看到了一百万人在歌唱,在祈祷,就像那咆哮的大海的回头浪。我看到了他们交换和平的标记,他们从数以百计分散在人群中带来圣体的牧师的手中拿圣餐。当圣餐面饼分完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那圣餐面饼掰成小块,最后就是小块和粉末,而人们找到一块草地跪着。但是,真正让你感到吃惊的是另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喧闹声。我想要说:一百万人安安静静。这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安静。这是与想像相反的一种情况。到某个时刻,圣餐仪式的程序正好就是那个: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做祷告。在那摇滚乐音乐会用的大音箱里,你听到教皇的疲劳气息。而整个周围鸦雀无声,他们一动也不动,没有一个小旗在挥舞,所有人都静静地停在那里。人,这是何种音乐。在最后的祝福仪式时,连摄像师们都划十字,这说明了一切。高级教士们开始同各类名人和政界人士一起退场。只有保安人员留在那里不动,他们戴着他们的墨镜,在某个地方别着手枪,他们永远要奔向发生故事的地方。
这样,在那上面几乎只剩下了教皇。那巨兽唱着一些宗教歌曲,模模糊糊地像西部电影,因而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他靠着祭坛,停在那里听着。也许他早就停止了激动的习惯。当然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正好是时候。接着他注视着那巨兽,并向大家致意。长时间地、慢慢地。他转过身,走了,迈着筋疲力尽的步子,就像爷爷从桌子走到电视机前面的沙发时走的那种步子。只是他以在那里的那种步子走遍世界。到了离他本来要消失在那里的后面的幕布几米远处,他停下来了。这可以打赌,在那个时刻,数以千计的人会想到,现在他转过身来,现在他再一次看着我们,他在头脑中永远带走那样一张照片。
那是害了我们的电影。在电影片中总是在那里发生那样的事情的。如果人们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在门前不先停下来,转过身,说点什么漂亮的东西,那就是胆小鬼。教皇不是一部电影。他没有转过身来就消失了。
/* 50 */
最后的女明星
悲伤的拳击手
你走错路往右去,就到了意大利弗留利大区波尔德诺内省的瓦让特镇,走错路往左去就到了弗留利大区乌迪内省的杰莫纳镇。这些地方并不是特别幸运的。这里的山岭离奇古怪,走势无定,使风景和生活都复杂化了,对厚脸皮的人来说则是一个磨练的场所。在波尔德诺内省的塞夸尔斯,种植着优质苹果,并使人们记起流行的马赛克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们。有两千居民,其中一千人是不时地回来的移民。他们把马赛克带到了世界的所有各个地方,但是苹果他们不带走。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点名望。其余的事情就与他们中的一个人有联系,此人在所有各种意义上都是最伟大的人。他身高二点零四米,状态好的时候体重一百二十五公斤,穿五十二号的鞋。他没有苹果或马赛克带给世界。他带着他的拳头(三十七厘米多)和他的悲伤的微笑。他叫普里莫·卡尔内拉,在这里出生,到处都生活过,三十年前也是在这里去世的。那是在地震改变了一切之前,但是在他变成现在在他的坟墓上普普通通地、非常简单地写着的那样之后:世界拳击冠军。
他的故事很奇怪。而真实情况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经纪人对所做过的事情开玩笑地说:卡尔内拉几乎一半的胜利都是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夸耀。卡尔内拉知道什么事情,这是神秘的。但是,大概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偶然地进入那个世界的,他来自马戏团,在那里他做巨人的角色,从他们把他安排在拳击台上的时候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着这样一个人的面孔:这个人没有彻底弄清楚,那些人在他周围是在开玩笑呢还是严肃认真的。那是因为墨索里尼把他作为制度的胜利象征出卖了,那是因为拳击史是由最强者即美国人创造的。但是,如果你不开上汽车,到塞夸尔斯这里来转一转,那么你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就会是像悲伤的滑稽角色、受屈辱的意大利人那样的东西。他们总是让你看那个下流的电影片,在那个电影片里,他同一只袋鼠优秀拳击手一起作表演。卡尔内拉还打着领带,尴尬地微笑着。袋鼠这个时候开始打,以自己的方式,不过有点打的意思。后来是在电影(折磨人的影片)中当演员的卡尔内拉,理发师用斧子给他刮胡子,还有那些可能同尽可能小的那些人一起拍的照片。怪人卡尔内拉,他们给他一点小钱,剩下的则富了他们自己。当你问卡尔内拉对洛杉矶有何想法时,他用在电影中学会的英语回答说:在第三个回合我就把它打倒。整个儿就是一系列这类悲伤的事情。然而,在塞夸尔斯,是不同的。在这里,人们相信。最后他们也说服了你,至少他们说服了你几个小时。
每年他们都举办以其名字命名的一次杯赛,业余的最重量级的比赛。正如人们所说,这是拳击运动的健康部分。今年是三十周年,因此更加隆重一些。晚上有音乐会,上午有弥撒,然后有一个展览。卡尔内拉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很激动并且也让人激动,恩佐·比阿吉讲述那个人是好人,首先是一个好人,而其余一切都是运气(他并没有完全说这些话,但意思就是那个)。如果你找遗物,那么你找到他的一双鞋实际上相当令人吃惊放在玻璃下面;他最后买的别墅,适度的豪华;还有许多照片。地震把老酒吧带走了,生前他总是到那里去,那个神秘的杯子也没有了,他一直是用那同一个杯子喝酒的。然而,那些记忆,是不可能被带走的。无论谁在那里停留,都留下一个记忆。这是那些成为名人的美好的东西:他们过的生活送给人们难忘的时刻。有时候在某个姿态的过程中是算不了什么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一生的马赛克中,就是燃起激情的东西,就是不可磨灭的美妙之物。那是一些小孩子,卡尔内拉用一只手把他们举起。或者他把上衣借给小孩一会儿,小孩穿在身上一直垂到地上。去对他说,他的对手们使人感到吃惊,在一个回合与另一个回合之间,在那个角落里,他们把吸满脏水的一块泡沫塑料给了他。这要倒霉了。最多使你觉得他不是很漂亮,在那张照片里。是的,他像好莱坞的一个明星,但是他们应当把照片修一修,他根本不漂亮。但是,他们说,他的眼睛善良而温柔。对一位职业拳击手来说,这是奇怪的命运:他的温柔得到了纪念。是的,他还发生过可怕的事故:在拳击台上打死一个人。此人叫厄尼·沙夫,别名〃海虎〃。他最后看见的东西是那有着温柔的双眼的巨人;他最后没有看见的东西是他永远告别的那致命的拳头。
这是塞夸尔斯的空气。但是在展览会上安装的监控器前面,你看见在放卡尔内拉在拳击台上的形象,你忘记那袋鼠和在那里的所有那类东西。他防守得不好,笨拙,但是他攻击得好,他很好地利用了他所具有的力量。他在跟前,就他那种体格在那里,真不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可能是他们送给他胜利,但是可以想像的是,他们正是乐意这样做:倒在地上总是比冒那样一个人的认真的拳打危险要好。正好能躲避他的打击。那么,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一天变成了历史性的日子:1933年6月29日。夏基当时是世界冠军。他不是拳击运动的大人物,他有点疯狂,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拳击手。他不是很想同卡尔内拉比赛,这有点是因为他并不觉得那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有点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件太认真的事情。在那一天,他曾经在〃海虎〃的那个角落里。他并没有忘记他在那里所看见的情况。他走上了拳击台,他应当清楚他完全是要输的。事实上他输了。比赛进行到第六个回合的第一百四十七秒钟时,卡尔内拉突然打出一记致命的上钩拳。人们随即喊出这是个丑闻,把那记拳称为魔鬼拳。夏基,当他醒过来记起家里的地址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从来没有挨过这么有力的一拳。〃他的经纪人由此认为,在卡尔内拉的手套里放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而在这里,呼吸着塞夸尔斯的空气来写作,你想到的惟一东西就是:全都是谎言。
世界桂冠,卡尔内拉后来在同贝尔一个会干的人,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女人的一场比赛中失去了,那场比赛给他的形象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他当时勇敢,很用心。他十一次倒在地毯上,如果你看到那拍下的片子,你会站起来叫喊让他们停止。但是他仍然在那里,让人宰杀,在眼睛里没有温柔,只有非常的尊严。其余的年月就消耗在赚面包方面了,尽其所能。在西部电影中,或作滑稽表演。在全世界转,走到哪里算哪里。后来,为了死,他选择了这里,这个他的故乡。他是从这里出去的,又回到了这里。在某些人中有这样一种坚定志向:为生存而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他应当就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应当是有点这样。在他的墓碑上还有他的兄弟的名字。他叫什么呢?那要看看。这是没有大的幻想、但是有条理的人,从不动摇,而且有条不紊。例如,卡尔内拉在1967年去世,并不是随便的哪一天,而是6月29日。这是他成为世界冠军的同一个日子。该是生来就如此。这些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 51 */
最后的女明星
玛丽亚·卡拉斯,在逃的美丽
她有着一种嘲弄人的美丽。从一张照片到另外一张照片,出现又消失的那种美丽,使你好奇地要知道她的真实面目究竟怎样。她曾有这样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标志了歌剧史上永远没有治愈的一个创伤。读一读关于她的那些书,你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特别命运的幸运使她没有普通幸福的快乐。她尽可能以最无声无息的方式去世,世界上所有各报吃惊地宣布,二十年前的9月16日,卡拉斯在巴黎的一所豪华住宅去世。现在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又适逢那个悲痛日子的二十周年隆重纪念,需要向人们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法医治的思念和这种后爱的广泛表演。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让大家都安静几分钟,把她唱的《爱我吧,阿尔弗莱多》放到空气中,然后全部关掉并走人。但愿还在那里停留一会儿,而只让一句话掉落在那里,正好是作为一种征兆她并没有漂亮的声音。就这样走了。
有一次,我把一个坏磁带放进录音机里,那里面有她和泰巴尔迪女士,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唱。〃那么好吧,我将走得远远的〃,卡塔拉尼所作歌剧《沃利》(Wally)选段。并不是为了疯子般地回到早先使歌剧的人民分裂的那种竞争上去,而是有助于弄明白。那么泰巴尔迪先唱。真妙,卡塔拉尼作的歌剧她唱得好,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一页她正好拿手,但是也必须善于这样唱。那声音进入空中,犹如一幅完美景色的轮廓,这个景色在亮光的照耀下。描绘这个景色是为了表明完美无缺是可能的,而且是温柔的。这是让人出神的一种东西。接着有一阵短暂的黑暗,后来就是卡拉斯。开头的那些音符向你扑面而来,你猛然感觉到的是,魅力突然中断了,那个风景好像暗下来了,那种完美无缺的想法破灭了。在那个声音里,有一个小灾难:你看到那种美奥林匹克的、平衡的、有序的美的某种概念崩溃了,在那废墟中你处在你不认识的某种东西面前。仿佛是受生命驱赶而在逃的一种美丽的某种东西。而眼前,你曾经看到的那种迷人的风景在那里已经不再有。因为它已经在你身上。
①盖尔尼卡,西班牙北部小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7年4月,同佛朗哥勾结在一起的德国飞机将这座小城炸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他的一幅名画译注。你是风景,她用那声音唱卡塔拉尼的好歌,这就是一切。前面没有任何东西,每件东西都在身上。为此,现在是很难忘记她的:她的声音曾经是声学的盖尔尼卡①:她撕破了某种东西,而又没有能使人忘记那美妙惊奇的缝合。她走上舞台,撕开那美丽的外壳,以便释放音乐的那种爆炸。是的,但是还在如此之前:生活逃出那种使人安心的优雅的禁锢,历史从遥远的地方跑到你身上来,仿佛多年来它就在找你。她从来就不是唱,而是讲。她有这种神秘的能力把一个故事的噼啪响声聚集在每一个音符中。她能够把整个的命运包含在一个句子里。她的维奥莱塔·瓦莱里没有唱一个不是写着她的死的音符,而当她死的时候,又有在音符里到处逃出的生命。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当爆发出她的〃我永远自由〃的时候,能闻到临终的气味在她死的那张床的周围香槟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但是我知道,如果那是一种技巧,谁也不能再做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她大概是歌剧表演实践从未达到的现代化顶点。这是一种超出习惯和传统的先驱者的旅行。它把所有人带到外面一个地方,在那里,歌剧唱法的有点庸俗的规矩被抛弃了,而有助于可以说是对故事的直接拿来。她用其特殊的声音质量不是为了组成一种秩序,而是为了主宰一种爆炸。她解放戏剧,并不把它局限在自己的能力或一种美的抽象概念之中。于是她摧毁了博物馆,歌剧变成了发射出去打伤人时的活的历史碎片。她唱,并不是后来的仪式,而是发生的现在。也许就是因此,我们无法忘记她这是我们没有进行的革命。
/* 52 */
最后的女明星
废墟中的圣方济各
你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你所看不见的东西:不再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