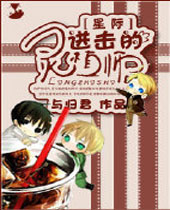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为英国杯决赛最常见的结果。以一句漂亮的射门在门梁(当时没有)下进球的是那位莫顿·皮托·贝茨。还有他的一张照片:他身穿带条纹的漂亮球衣,手拿一个板球棒。这也是为了告诉人们在这个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国家体育项目。
当我看到迪·马泰奥在开赛的哨声响后还没有过一分钟就同出一辙地进球的时候,我想起了莫顿·皮托·贝茨先生的那个神奇的进球。在从赛场四分之三的地方向前推进,他准备惯用的边路带球过人,他发现前面没有任何人,他不敢相信地往前带球,加速。他想这是一个玩笑,自问米德尔斯伯勒队的防线到哪里去了呢?他甩掉了所有人,果断地用右脚脖子劲射,球在横梁下面飞进了球网。蓝色的大草原爆炸了。那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挑战,然而在球场上往往看到的是教区水平的足球。当他们拿得到球的时候,他们在后场拿球,然后大家都奇怪地看着那球,该怎么办呢,并没有清楚的想法。像省级电动台球似的球从中场回传,守门员直接把球踢出,边线球。就是这样的东西。〃博罗队〃(大概是米德尔斯伯勒队的别名)有两名巴西球员:埃梅尔森,踢中场,像状态不佳时的索萨;尤尼诺,在四分之三后场转悠,有上帝般的后跟传球,不过也只是抹点奶油,稍稍多点。前面有拉瓦奈利。球总是给他传到门旁边。他要等二十分钟才能有一次该有的传球;他冲过去,倒在那下面。舒展一下身体,就完事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花大钱买下了他,那就是当中场候补队员米克尔·贝克上场的时候。此人是这么一个人:在到区域限度时才开始停步,而当他停下来时,他已正好在半场。他非常注意不要弄乱头发,实际上他在整一场比赛中都越位。由于切尔西队是由古利特派上场的佐拉在前场无精打采,维阿利坐板凳会让你看到好玩的,你想想,这场比赛进球了。然而,这是英国杯赛,也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发生了。例如〃巨人杀手〃的故事。我来解释一下。要知道,这个杯赛是一件大事,有五百多个足球队参加的一场挑战。从第四级以上的队可以随意报名参加:大家都可以梦想。而比赛制度仍然是很原始的,因而也是很有魅力的:直接对抗赛,谁赢谁过,如果打平了,几天之后再赛一场。这种制度的无信义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巨人杀手〃现象,这也就是英国人喜欢杯赛比冠军赛多一千倍的道理之一。〃巨人杀手们〃就是上场对抗强队并荒唐地取胜的那些冒出来的小队。例如,1933年,阿森纳队被沃尔索尔队以2∶0击败。英国广播公司BBC(权威的BBC)以为那是一个玩笑,因此没有发消息。凶狠的记者们算了两笔账,他们说明,买沃尔索尔队整个队一块儿买比为阿森纳队的人买鞋的钱花得还少。
如果还记得的话,显而易见,这样的比赛延续了多年。这是一种悲剧。正如曼城队教练马尔科姆·阿利森在被哈利法克斯镇队(第四级队)以漂亮的1∶0击败之后所作的很好的概括:〃丢掉这场比赛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肯定是非常相似的。〃走完了布满地雷的道路,两个队到达了决赛的神话:只用一个词便可以概括:文布利。
文布利,对英国足球来说,就是六十年代意大利家庭的大厅,神秘的大厅。这种大厅全年都关着,沙发上用塑料布盖着,家具变陈:每年开三次,为了重要的活动。因而,这是一种神话。在文布利只有国家队的比赛(所有各场比赛都是)和英国杯决赛。是一个很丑的体育场,也不好看球,到那里还不方便。但它不是一个球队的体育场,而是整个国家的体育场。他们早就决定了那会是一个传奇。那个体育场于1923年落成,自然是为了英国杯决赛。当时来了二十万人,当国王准时地在开赛前一刻钟在那里出现的时候,连球场也看不见了:完全被人盖住了。骑警们来了,用了四十五分钟才把足球场清理出来。在那许多马之中有一匹是白马。那匹白马名叫比利,十三岁:由于它是白色的,他们就把它作为象征,因而它成了英雄。那场决赛当时就叫做〃白马决赛〃。你看文布利怎么样:连球都还没有踢一下,就已经产生传奇。博尔顿万德雷斯队2∶0取胜。一直到球场边上都是人,连踢个角球都要用胳膊肘挤出地来。在中间休息时,为了拿一瓶可口可乐,我也要用胳膊肘开路。蓝队或红队球迷,毫无问题地在一起痛饮啤酒,相互拍打着脊背。他们是一群奇怪的观众。他们不断地鼓掌,为最起码的事而鼓掌。有许多胸部停球:肯定博得鼓掌。切尔西队的中锋休斯专于一种完全特别的动作:在四分之三后场得球,回转带球至区域界限,然后很神气地停住,转过身来,把球向后回传三十米:下面是热烈鼓掌,可想而知。
下半场进行到一刻钟时,比赛乱了套,英国足球的美妙之处也出来了。大区域,从这边到那边,一阵又一阵纯粹的竞技,什么队形都见鬼去了。对像佐拉那样的一个人来说,那真是天堂。开始像病毒那样进入博罗队的防区。这里来一个两腿间的传球,那里来一个假动作,其他人就只能在他后面流汗了。当他看到那些人都筋疲力尽时,他来了一个大胆的动作:回转过了四个人,射门:正好守门员紧握拳头没让他得胜。无论如何,在第二个进球的行动中有他的小传,像打冰球的办法那样,他在离球门两步的边上干,牛顿把球装进空门。离结束还有八分钟。第八十八分钟正好是看见维阿利进场的时间:悲伤、孤独的结局。其余就是欢庆场面,穿着红色衣服的孩子们流下热泪,两眼通红,而穿着蓝色衣服的家长父亲唱着,把能唱的全都唱了,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古利特,穿着黑色套服,在球场中漫步。他很平静,似乎在想着,如果在那里种上玫瑰,或者但愿是一个漂亮的菜园子和一个喷泉,将来要看。他也可能是愉快的,不过他穿着闪亮的无跟皮鞋。这样,完全是另一回事①。
①1998年2月17日维阿利接替古利特的位置坐在切尔西队的板凳上。也许现在古利特也要踢一踢球译注。
/* 48 */
最后的女明星
伟大的母亲波兰(一)
假如是一本书,那就已经有个书名了:漫长的告别。这很难说,如果有一个发生奇迹的世界,那就是这个:七十七岁的教皇,决定到其祖国作一次宗教旅行,他心里想的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人道的事情:告别自己的国土,再去看看她,带回最后的一些记忆。在布置豪华并有电视转播的许多正式仪式中间,谁知道在他的眼中和在他的心里有多少小仪式。这些小仪式是他周围的任何人都看不见的,而他则将在其记忆中看见多年。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克拉科夫。这并非偶然,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比任何其他城市都曾经更是他的城市。他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在这个地方成为牧师,后来成为主教。这是他的根。这是一座优雅而安静的城市,靠着大河维斯瓦河,仿佛是安静的灵魂跳出两道弯。这是皇城,圣人之城,大学之城,衰落了的大型钢铁企业之城。纳粹分子因为没有时间或不想摧毁它,因而放弃了它;俄国人进入该城时连开枪都不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留下伤疤的极少数城市之一。这是一个瑰宝。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哥白尼,第一个提出世界如何转动的人,曾经学习过。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斯皮尔伯格拍摄了《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一片的大部分。根据新闻报道,就是在这里,卡罗尔·沃依蒂瓦十八岁时从省里的一个小地方来到这里:那时他到这里还是学生,四十年后他再去那里时,他是教皇。
你今天正在回到这里来,那你就明白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他们期待着他,把城市布置成白色和黄色的旗帜,在白色和红色的波兰国旗旁边随风飘扬。歪歪斜斜的或宽大的轿车到处停靠着,信徒们从车上下来。在飞速跃向西方并整个儿歪歪斜斜地竭力爬上福利上坡路的这个世界的地面上,到处都张贴着他的面孔。在利瓦尔商店的橱窗和哈特比萨饼店都有他的照片。在卖水龙头和床单的小铺子里有他的照片,这些小铺子的橱窗好像是从来不再打开的抽屉。在现实社会主义式的住房的数以千计的窗户上有他的照片,这些房子的窗户没有百叶窗,有许多双层玻璃,门面是灰色的,所有窗户都一个样,大门是黑色的小门。人们用透明胶纸把他的照片贴在玻璃上,也有人再加上一些圣母像或者一块刺绣小垫布谁知道为什么以及圣波得广场的明信片。也许他根本就不从那里经过。但是,这没有关系,仿佛他们关心的是让人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他正在到这里来,他们知道这个事儿。用得最多的照片是身着白色衣服的沃依蒂瓦,一张微笑的坚强面孔,伸出一只手来招手致意,另一只手靠在像是一辆汽车的顶棚的东西上,一种喷了蓝色漆的东西。衣服袖子有点往上了,这样,在靠着蓝色钢板的那只手上露出一只手表,这手表一点也不豪华,而是一块真的手表,人们所有的那样的手表,工作的人戴的手表。那块手表,我还记得它。我记得开始看到戴着手表的一个教皇而产生的那种奇怪感觉。我想要说,并不是你期待一位关心几点钟的教皇,可能你想像他忙于永恒,而不是忙于时间。但是他有手表。然后,还有教皇滑雪,在游泳池、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那些照片。但是在开始时,正好是在开始时,你看到了那张戴手表的照片,事情就会是这样的。
我偶然地在一台开着的电视机前走过时突然看到的那个教皇,并不是同样的教皇。这是在这里周围山上那个寺庙做弥撒的实况转播。没有手表,没有微笑。是一位疲倦的教皇。总是在说他,到处都可以读到他。然而看见他,是不同的。修女们在唱歌,在云彩低飞的一天人们拥挤在那个教堂外面,各类高级教士在祭坛的周围,在中间就是他。总是有点驼着背,面孔发红。声音开始时有力,后来就滑进只有老人的声音才有的那种漂亮的脆弱。他的动作缓慢,让你着迷,你无法使之同他到处从各个窗户向你致意的那种自信的致意合拍。没有手表的动作。在做弥撒举扬圣体中,当他拿起圣餐面饼时,仿佛举起一块巨石。他把那面饼举得高高的,在头上,同时闭着眼睛,而且有更多的东西。他尽可能用全部力量抓紧那些东西,仿佛他想消失在那黑暗之中,或者仿佛那个动作让他付出巨大的辛劳。谁知道为什么,会让你想到,如果有做那个动作的一种正确方式,那就是那个方式。没有任何其他方式。
他年轻的时候有着好莱坞明星那样的一张脸、出色的演员天才(他们说)和办什么事都认真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1946年11月1日他被任命为牧师,两天后他举行了作为他的第一次弥撒的那个弥撒:他是在维斯瓦河畔他的那个区的教堂里举行的,那是一个鲍斯高慈幼会教堂。如果你要去找那个教堂,你不会找错的:球场,辅助圣母玛丽亚,令人目瞪口呆的建筑那只能是那个教堂。里面挤满了人。离弥撒开始还有十分钟,我又看到了在意大利我看见消失的那种场面。大家都在那些忏悔室前面排队,十个人的长队,有小孩、老人、穿工作服的、带着儿子的爸爸,大家都在排队忏悔罪过。牧师有着漂亮的声音,他们几乎不断地唱着来自农民土地的曲调。以这种奇怪的语言读出来的上帝的话是可怕和甜蜜的混合物,你一点儿也听不懂,但是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也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上帝。不那么使人相信的是:这样一个教堂能拥有那样的灯和那样轰动人的镶嵌,我连想都没想去弄明白它。
在周围,城市里熙熙攘攘,有越来越多的童子军或类似的东西,警察,栅栏,旗帜,兴高采烈的等待。在河边,成群的老年人回想着过去,在胶布棋盘上下着棋。他们几乎都头戴一顶草帽,就是农民戴的那种草帽,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戴着Lakers小帽:就是这样,各种世界消失,没有让人看见就从最没有意义的枪眼溜出去了。
我到大主教府去了,想看一看沃依蒂瓦度过其主教年代的那些房子,但是他们把那个地方弄成了一种博物馆,我就跑了。于是我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过城市去看一个坟墓。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漂亮的故事。我想要说,在诸如封圣、周年纪念、心脏外科医院落成等许多隆重活动中间,教皇还插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确是漫长告别的美好姿态:在某个时候他到城市公墓去向其双亲致意。在照片中,父亲身着制服,有着一副穿着制服的男人的脸孔。母亲有着本地女孩的那种眼睛,散落在让你感到沮丧的那种美丽的白净面孔上。他们的墓是灰色大理石的,光亮,摆着红玫瑰,数十支彩色小蜡烛。周围,他们正在那里搭些小台子,是为当局或者摄影师或谁知道为谁的。无论如何,有点悲伤。他们本来可以让他安静点,至少在那里,不是吗?在那边过去一点儿,如果你找对了,你可以找到塔德乌斯·坎特的墓。那里有一座坐在学校课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的一个小孩的塑像。这正好是新闻报道的东西。
天空中,不时地有一架直升机在啪哒啪哒地转着它的桨板。这总是一种假警报,但是人们仍然抬起头仰望着,喃喃地说着:教皇。实际上,教皇于十九时准时到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飞机场降落,并开始进行令人难忘的一系列会见。这使人要问,如果不是一位疲倦的教皇,他会做些什么事呢?明天,一个大草坪等着他,那个大草坪离市中心不远。这是他召集的最后一次一百多万人的集会。这将是他同他的人民的最后一次大拥抱。如果你现在到那里去,你会碰到小孩们在玩小滑车,狗在跑,一家一家人在散步,修女们在抚摸土地,像一场足球赛之前的运动员们那样。在变成传奇地方的数小时之前,这些地方还能是平常的地方,这总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
/* 49 */
最后的女明星
伟大的母亲波兰(二)
你看到这样一种东西和那可爱的老术语〃大弥撒〃(十一时的那个弥撒,有本堂神甫的那个弥撒),那就会让你永远成为粉末。祭坛上的教皇,数十名高级教士,特别是一百万人。这就是说,如果你早晨五时醒来,从窗户上看,你便看见人们行进中的队伍,而离弥撒开始还有五个半小时。这就是说,在你住的房子里,那天大家都出去了,真的是所有人都去,包括在第三层的正忙着那些偷来的汽车零件的那位,从来不出门的坐着轮椅的那位奶奶,在窗户上没有贴上教皇照片的那位会计,晚上晚回来、脚上圣特鲁佩兹式的大木筏子还弄出噪音来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一百万人,就是说所有人,看见他们在那里大草坪上,似乎是一头平静的巨兽。它会有力量连根拔起任何东西,而它在那里却是在参加某种和平的仪式。这是一场奇怪的戏。他们穿上了他们的制服,这是他们本地区的服装,或者是院士式的貂皮。他们挥舞旗帜和横幅,没有任何东西的人至少有一条白手帕在空中飘扬,或者是高举张开的一只手在致意。教皇非常熟悉他们,他让他们激动不已。他坐在他的教皇车上,穿行在正好是那巨兽的肚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