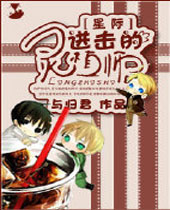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52 */
最后的女明星
废墟中的圣方济各
你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你所看不见的东西:不再有色彩。当你终于进入不能进去的那个大教堂的里面的时候,你到处碰到的灰色首先向你讲述发生了什么事情①。悲惨的半明半暗,一切都熄灭了。在厚厚的白色灰尘下面,乔托②壁画的颜色有时候是非洲地毯、加利福尼亚机织割绒地毯式的令人羞耻的颜色在低声呼喊。在那高处的蓝色的签名还有点在闪亮:其余便是中断了的、不再做声的节日。
①1997年9月间,地震开始打击意大利中部一些地区,至今尚未停止。阿西西是受灾地区之一译注。
②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译注。
③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最早的画家之一,相传为乔托的老师,其作品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前奏意义译注。灰色而没有色彩,是那个在大祭坛的位置上的瓦砾山。抬起眼睛,你看见拱顶上的一条裂缝,后面,房顶,安安静静地入睡了。在那座灰色的山里,有留下的契马部埃③后期作品之一。看上去这样,可能会是任何东西的废墟:邻居的车库,旧的明星电影院。现在他们在那里做了超市。任何东西。而恰恰相反。灰尘、瓦砾、石块、油灰、垃圾以及齐马布埃,这一切都被一个十米跳搅拌在一起,被震动的地球不合逻辑的愤怒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飞行中扔下的炸弹。如果你想一想,那是一种凶残的美。也许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座灰色的山我会原原原本本地拿来,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它。这是现代艺术。
另一个裂缝正好在正门的上面。跨进大门,你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砖头就在那上面悬着,毫无道理,那会是在开玩笑。地上,是一个奇怪的形象:他们把瓦砾去掉了,在那个地方已经铺上了床垫子,不过是那种破旧的床垫子,像兵营里用的那种,带白色和褐色条条,一个挨一个地放着。你觉得有一会儿思想糊涂了,因为在那里,你觉得是一个难民营。我知道那一类东西。忽然你又想像某些绝望的人的漂亮故事,那教堂给他们住下,也算有了个房子。在幻想中,两个灾难相互交织。总而言之,是一个奇怪的效应。相反,这只是意大利式的机灵,是工作中的一种聪明才智如果从上面掉下点别的什么东西来,那就会掉到软的东西上。整个儿就是这么回事。
在一个角落被遗忘的哨兵里,还有一个牌子通告:肃静。说真的,在那里面有那样一种安静,似乎该在上面写上:劳驾,请谁说点什么。大概你只会害怕窗户呼呼作响和教堂的那一块嘎吱作响。一切都是那样的超现实,在床垫子上走着走着,我一直走到了另一个自相矛盾的幸存东西:一个导游电话。我想要说,一个像电话那样的圆筒子东西,但是,如果你往上拉,就会有一个声音向你解说,把你的任何激情都一扫而光,把任何魅力都化为灰烬,使得对那个地方的哪怕是最小可能产生的热情也化为乌有。但是它解说。好吧,在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个导游电话,那上面全是白色的灰尘。而我想到,在那个吊着的、中断了的、没有人在的世界里听到了那个声音,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像是在掉到湖底的一辆汽车里的收音机那样的一种声音。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放进去,以便让它说话,那是值得的。什么呀,显而易见,那是关掉了的。整个周围就是黑暗、乔托和肃静。是一直在那里的、受伤了但是还活着的大教堂,给了你一种奇怪的感觉。而如果你想要描绘这种感觉,那么你只会想到:病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乱七八糟的头发,最白的手,他们的眼睛有点看着你,对你微笑着,但是从窗户进来的光使他们觉得不舒服,而那个收音机,劳驾,你把它放低点声音?就是这样一类东西。
最后,我又往后回来了,还是走在那些床垫子上,我一直走到我去那里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地方:我走到了一幅向鸟儿们布道的壁画下面。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消防警察客气地通知我,向我说明正是在那上面砖头就像花边一样。而我在那里正是为了这个。检查一下待在那里是不是好。那个壁画。因为那不是一幅壁画,而是一个象征。
我多年来不曾有过一点最小的怀疑:有一天圣方济各向鸟儿们布道,那些鸟儿在那里听他讲,只有当他结束了讲话并向鸟儿们祝福的时候,鸟儿们才飞走。我觉得对于能够写出《创造物的赞美歌》的一个人来说,这是绝对合理的事情。后来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基阿拉·弗鲁戈尼所著《一个人的生活:阿西西的方济各》),我发现大概事情并非确实如此。那本书说,在那个时候,严禁世俗人员布道。方济各那时是世俗人员,他遵守规则。他一直到罗马去找教皇,要求获得让他及其他修士们布道的特别许可。请注意,正是在那次旅行中发生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而如果读一读当时的新闻纪事,那么那些鸟儿都有确切的名字:鸽子、乌鸦、灰雀……而如果你研究一下中世纪的肖像学,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些鸟中的每一种在字面上都是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于是,通情达理地想到的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是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具有破坏性而更少具有诗意的一种奇迹:一个人,不是一位牧师,在路上停下来,开始向穷人(鸽子、乌鸦、灰雀)布道。人们也停下来。到某个时候甚至开始来了一些先生(新闻纪事说,当时还有秃鹫和一些猛禽),大家都被那个人和他的话所打动。虽然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发生了:他们要讲述这件事,为此他们要找到一种方式使用属于他们的文明的暗语。
那么,有人要问:怎么回事,像我们的文明那样的一种受过启蒙而明智的文明,后面还带着像向鸟儿们布道的故事那样的一种故事,而没有揭穿它,不记得需要讨论它呢?回答:乔托。那本书说,在方济各死后,曾流行着关于他的生活的数以百计的新闻纪事。由于这个神话在发展,异端的危险就在那个角落后面。于是方济各总会决定,最好还是把故事固定在一个正式的、权威的、勿庸争议的版本上。1266年决定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圣方济各的故事,就是由博纳文图拉在《最大的传奇》中所写的那个故事。其他所有故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发现,我们就会对其一无所知。现在,那个故事就是乔托在那个大教堂里讲述的故事。说穿了,那个大教堂是一个明智的中间选择,以大家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和一本书不可能具有的戏剧性,加之以一个特殊的故事,并消灭所有其他故事。他们选得好,乔托似乎就是为了做那种事情的人。他使用天才的透视画法,突破了他的想像,给世界看到某些东西在当时应当看来是潜在真理一类的勇敢行为。如果你产生一些怀疑,那么惊奇就会使你消除那些怀疑。
因此,那个大教堂,就是对一位世俗者来说,也是一种象征。而那幅带有方济各向那些无名的小鸟们弯腰的壁画,就是那种象征的概括。你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东西重复了数千次,给了所有叙事文学作家的职业一种意义:当他们有力量做这种职业的时候,那些故事传下去能够抓往事物真相的虚假东西。他从来没有做那事那没有关系,但是方济各是向鸟儿们布道的一个人。如果你注视那幅壁画,那么其异常的核心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了。而如果写叙事文学作品的人能够通过美丽和戏剧性来使你忘记通情达理的小心谨慎,那么你只能感谢他。他确确实实地尽了其职。
我正好就是这样到了那里去感谢的。也就是说,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一切都正常。那里在继续低声地讲述着那个故事。那里有地上铺的床垫、那种黑暗、埋掉一切的白色灰尘、头顶上使人害怕的那些裂缝、从来不停的地震,正是在那里面燃起失去生命的记忆。然而那个故事继续在讲述。声音软弱,但是你听得见那声音。
外面,大家都在护理这个大病号。数吨的吊车在空中旋转,普通的人们头戴安全帽,戴着太空焊工式的奇怪眼镜,做着相当奇迹般的事情。在修道院内,每一堵墙都有裂缝,损失的清单没有完。饭厅以其方式显得很热闹。一切都准备得很好,所有餐巾都叠成一个样,每三个位子就有一瓶矿泉水。在每个位置上杯子都翻过来扣在盘子上,一张很长的桌子,虽然贫穷但是完美,带有其正常年代所安排的那种协调。里面爆炸了,到处射出墙皮和灰沙。谁也没有再碰任何东西。就像一张唱片不转了那样。
外面,大教堂门前空地前面,有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在修建。他们是修复者。他们仔细翻查瓦砾,像淘金者那样,他们找到一些带颜色的小块,然后,慢慢地他们拼出了图案。许多塑料筐排在一起,像鱼市那样。只是在里面装的不是沙丁鱼和鱿鱼,而是由许许多多不起眼的小块重新拼起来的圣鲁菲诺的面孔,或者是装在玻璃纸小袋中的圣安东尼奥的手。在一个筐子里还有圣方济各,他的面孔。还差一点,正好差一些碎块。其中差一块,大小如同一只眼睛,而且正好就是圣方济各的左眼。它在正面大门上面数米高处。数世纪以来它就一直在那上面。而现在,在那里注视着你。好像你没法待在那里,你转过身就走吗?
/* 53 */
最后的女明星
用吉他射击的人
如此开始。数十名流浪者,挤在一节火车厢里。这里充满臭气、酒精味,漂亮的故事,乱打乱闹。这是一节货车厢。闭上眼睛就可以闻出味儿来。火车开向芝加哥,要通过四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话。即便是说他们,他们也说话。他们说:我们,从哪里来吗?在生活中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呢?然而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唱一首歌,歌词说:thistrainisboundforglory;这列火车走向光荣,thistrain;这列火车。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一股热情。到了某个时候,有一个人爬到外面,一半在外面,吊在车厢边上,两只脚吊着,离地面一点,真像叫人害怕的一面旗子。当火车减速慢行时,他往下跳,跑着,飞跑中接过旁边递给他的小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到了车厢顶上。风在吹,风景在走。那个人随身带着一把吉他。他弹拨了几个音符。在那上面,车厢顶上,有另外三个人。他们靠近他。他们看看天空,他们想:要下雨。这是新闻报道中所称的〃明尼苏达天空〃。云彩,然后是密布的云彩,然后是一阵大雨,洗刷了下面的一切。于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拿上他的毛衣,把它递给拿着吉他的那个人。他说:下雨会把它淋坏的。那个人把吉他套在那件毛衣里,仿佛是一个小孩子。于是,另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衬衣递给他。还有那第三个人也脱下他的衬衣,虽然他的衬衣脏了,那也没有关系。火车在倾盆大雨下奔驰,车顶上有那四位光着脊梁的人,还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厚厚的衣服焐热了的一把吉他。如此开始。
带吉他的那个人是伍迪·格思里。他的自传体小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如此开始。该小说多年前已在意大利由萨维利出版社出版了,现在〃马科斯Y马科斯出版社〃重新出版克里斯蒂娜·贝尔泰阿的译本,并有阿列桑德罗·波尔泰利作的有益的前言。这是一本奇怪的书,奇妙得不完美的书。这是属于这样一本书:出版者会用许多合乎道理而又是破坏性的手术把它弄成碎块。像一位醉汉骑车人那样到处摇摇晃晃,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刹车,同时又像一列没有站的火车的铿锵声使你进入催眠状态。最后你是在旅行,并不舒服,然而是在旅行。在那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种无法抗拒的真诚使一切都变得可以饶恕。当你看完三百页之后碰到〃他的嘴唇在我的脸上犹如蝴蝶翅膀一般〃这样一类句子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好像那种句子多美,但是这类句子结束了使你厌烦的前两百页。
伍迪把他的故事放进了那本书,或者至少是他多么喜欢讲述他的故事。他来自一个叫做奥基马的城市,然后用了几十年才认出他那个流浪儿子的伟大,也就是他为了忘记他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全部时间。他的家庭的兴衰似乎是由最优秀的斯坦贝克创造出来的,而那却是无情地准确讲述某种美国的一种典型而真实的雕刻文字。先是富裕人家,后来倒霉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从零开始重来,然后永远消失了。母亲在一家精神病医院里要死了,父亲逃难到了得克萨斯的一个角落里,要做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维持其简单的生活。这是野蛮自由主义的美国,没有网子,在那里,富裕和贫穷像沙尘暴那样毫无道理地迅速通过。命运在住房起火、城市产生与灭亡、战争爆发这些强烈震动中前行。这是这样一种准确而疯狂的机制:这种机制产生金钱并无情地排除人类的破烂,使他们变成寻找生存可能的流浪族。伍迪曾是那些破烂中的一个。他有一把吉他和创编歌谣式故事的惊人才能。他就这样讲述他自己的和那些人的流浪生活,他做的好像别的任何人、包括斯坦贝克都做不到。他用汽油桶那样的声音唱,总是在时间上搞点名堂,甚至仿佛那节奏对他来说似乎是开玩笑的东西。随着年代推移,他获得了声誉,这本来也会使他能够东山再起,坐在美国某个可以饱食的座椅里。但是他应该是在里面有某种并不那么有利的爱好,某种必不可少的不稳定。于是他从不停息,可以这样说:他整个一生都是光着脊梁在奔驰的火车顶上。
他在书中说,他的父亲曾教他不要被任何人吓倒,他的母亲则教他要以不久未来的观点来看现实。好好地想一想,这正好是这样的两头:他使其生活、其政治努力、其作为见证人和艺术家的活动,都在那两头之间来回折腾。造反与对弱点的维护。勇敢与同情。再更好地想一想,就会明白,《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的所有各页也正是坚持停留在那种过时的剪刀之中。应当是这个原因,使那本书尽管不是一部杰作,但最终还是使你同那里连在一起,去呼吸那种空气,在那种热情、天真、真诚的氧气中再待一会儿。这是你几乎不再记得的一种空气。造反与同情是废而不用的灵魂之两个边缘,对一击两球的愤怒撞击来说是好的,而在这些时间里,你不再看得到这样做了。不再有善于想像这种一击两球的游戏者了。在历史的绿色台布上,玩的是没有生气的、由所谓通情达理的来回球所主宰的小比赛,连球袋都如此厌烦以至失去了它们的色彩,要明白哪个是你的球袋。伍迪知道哪个是他的球袋。在吉他上他写下了: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然后射出歌曲,而不是子弹,而同时给敌人一种明确且有名字的权利,让他一直带到崩溃,从不动摇。这样也是作为看到反面事物的享受不仅是义务。不是赞赏赢得胜利的无可非议的逻辑,而是他本能地在眼睛里看到会有人失败这种事实的绝对不合乎逻辑性。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不是一位哲学家。有一次在一场音乐会上用很平常的语言说到他:〃伍迪进到你的里面,把你想谁与你接近的那个部分拉出外面来了。〃这像教区新闻的公报里的玩意儿,因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