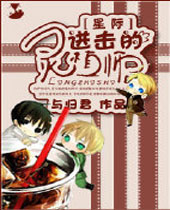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娜恕3渎鶥ladeRunner。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是否能真正喜爱这样一个世界。它具有正在到来的未来气氛,然而是一个噩梦还是一种享受,你不明白。这样你头脑发热时,你会倾向于第一种假设。但是,如果你试一试,你会感到有的东西还很有诱惑力。 有一天,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像流浪汉那样的人坐在一个街角的台阶上。我想说的是,那个人有五十岁左右,没有灰色上衣和耀眼的领带。他连眼镜也没有。他很脏,尤其是他无所事事。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这真是很少见的情况。于是我停下来看他。他脚上穿着耐克一类的鞋,穿着不知叫什么颜色的破裤子。他耳朵里戴着一个随身听的耳机。在他头脑中有音乐。这种事情总是使我感到好奇,我在意大利瓦莱塞省布斯托阿西奇奥市也是如此,我会给钱,以便知道听随身听的人在听什么。于是,这次我也试图想像。我心里想的只有一种情况:那个人可以什么都听。但是并不像伦敦的一位二十岁青年或意大利贝尔加摩的一位职员那样:他们那些人有许多可能性,但并没有所有一切可能性。这是不同的,这里,在这个世界的终端,那里一切都在转,都在过去,仿佛是通用清洗池的排水管。如果一个人在听随身听,那么在那个时刻,全世界所有音乐都可以在那里。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那个流浪汉在头脑中有着某种无限的东西。就像一种无限。于是很清楚,你在那个时候想着它:未来就将是这个。将是一个噩梦,一个非常美丽的噩梦。
/* 37 */
最后的女明星
《毁灭》:一个世界的目录
你们读一读《毁灭》。你们拿出这吉利的两万里拉,买一本《毁灭》。找到一个既没有音乐,也没有靠近噪音,而只是任何世界深处的地方,读起来。(最好你们的脑细胞没有超过四十岁,否则你们有滑倒在上面的危险。并不漂亮,却是如此。)
《毁灭》的女作者伊莎贝拉·圣科罗切,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她。讲了两句话,到了场,以软弱无力的播放节目的那种没有生气的节奏摆活了某些想法。她慢声慢气地说话,声音有点糊涂(benzodiazepine?酒精?或者简单地就是摄像机对着你而带来的效果?)。充斥发声器的没有任何聪明的东西。
《毁灭》是一本书(110页)。在那里面有着有才能的东西。如果布里奇有才能,那么在那里有着其双倍的才能。如果基阿拉·佐基有才能(这里我已经有所怀疑),那么那里有其十倍之多。这位女士写音乐,撞击声音,断奏交叉而不对称的节奏,组织混乱,她斜视,印刷不和谐。如果你让那本书演奏,你听到的是音乐,真正的而不是随便的音乐(只要在你的头颅里有沃尔托利尼或德尔朱迪切的词汇,那么你就知道多么美妙)。
有一种才能被理解为你工作所需的材料的本能掌握(不能教诲的东西,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而更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才能,今天二十岁的年轻人过分幸福地、筋疲力尽地拥有的那种形式的才能:理解世界的数量的怪异能力。我想说:他们是极为敏感的胶卷,是有一百个声道的录音机,是吸了毒的理解机器(没有吸毒的时候也是)。一位普通的二十岁年轻人,你在地铁碰到的站在那里的那位。十万人中只有一位的那个能写作的人,还原一切:是变成百科全书目录、无止境软件屏蔽的生活片断。是向你身上扑过来的输入银河。你感觉到冲击波,是一件不坏的快事。幸运者应当感觉到了这类东西,此时他们迎面传来罗西尼的音乐。他们在舞台上失去了知觉。
你们不要问我情节,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足以使音乐网站住脚,有点像老施特劳斯做的那样。他用了交响诗这种聪明的东西。在纯粹的音乐色欲还不够的情况下,不让读者跑掉的剧作艺术足以使之有理由翻开另一页而不放弃。这是职业(这是可以学会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用许多色情作为调料,加点暴力,喷洒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属于手工艺人的精明。这是给阅读增光的玩意儿。这种花招轻而易举,但永远不会不起作用。要成为真正能干的人,就应当获得同样的力量:在教堂里讲述一个婚姻故事或菲雷罗巧克力销售商会议。
我读了科特罗奈奥(是一位评论家)的文章,关于《毁灭》。他断然认为:〃粪块〃。终于如此。不再有他那种暧昧的搪塞,不再是横断信息、加了硫酸盐的俏皮话、按照非常奥妙的钱切利手册分配的祝福。直截了当:粪块。终于有一点清新空气。这会是一个好的起点,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想一想,弄明白。遗憾的是他没有这种愿望。(一般地说,评论家们都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在你面前,就像跟一个人下棋,这个人在走一步棋和另一步棋中间打电话,核对银行账,对着镜子检查一下淡红的假发不要滑下来,然后在某一个时候他们站起来就走了:他们从来不下完一盘棋,我担心他们以为这是赢棋的一种优雅方式。)
无论如何,我又想到科特罗奈奥那断然的〃粪块〃,我不能不明白那是有真的东西。这是在《毁灭》中,如同在最年轻的人所写的其他书中存在的一种东西。有点像是记录世界数量的超凡能力阻碍他们接近世界的本质(不大好理解的词儿,但没有其他词儿)。我要说:一部百科全书的目录包含世界,但不能帮助你认识世界:带来奇妙,但不能传授知识。是精彩的世界形象,但不是世界。《毁灭》是写得非常好的精彩的目录,而生活与它有什么关系呢?〃真实的理由〃到哪里见鬼去了?亲爱的老〃感觉〃又是什么呢?
是与往往在现代音乐(那种民间音乐,而不是那种有文化的音乐)和漫画面前具有的一样的感觉:技术越是惊人,世界的表演越是具有杂技特点而变得艰难,你离事物的中心也就越不那么近。一切都具有人为的、不可渗透的特点,使你想起各种娱乐公园的天才区分。迪斯尼乐园。如果白雪公主让你作呕,你喜欢震荡器和鸡奸而不是唐老鸭,那么你买一张票,进入《毁灭》。风格稍有不同,而内容是一样的。地方是分开的。
因此,一天早上你不小心把法规忘记在家里了,然后你也想:是些粪块。因为只要还有那些书存在,你就从一本书里期待更多的东西,本贾明以一个漂亮的说法说道:〃真理的英雄方面〃。从事物的心脏偷来的某种令人激动的形迹。往往有一个回声就够了,但是要来自那里。如果你什么也听不见,那么你最终迅速地想到的东西就是:都是粪块。而你正在想的东西是一种同时既真又假的东西。
文化新闻的虚假聪明把好人主义者同残忍的人对立起来,似乎文学就是一种斗鸡,有那些会写作的蠢鸡,在一种争吵中射出或多或少优雅或胆怯的几枪。这种争吵来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老先生们(最高就是坏先生们)以古老的智慧而行动,以令人赞叹的才干经营其平庸,这里打一棍子,那里又有点儿好色地轻轻抚摸一下,同漂亮女郎挎着胳膊在媒体人行道上散步。反正这漂亮女郎在良好时刻终于同别人上床,当然不是同他们的陈旧的东西。不过人们会转过身来,看着他们,那些过时的令人敬畏的老人,在那媒体的人行道上,对一个又一个的目光,他们那些人在消失之前会给以什么呢?如此显而易见,不能写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而每个人都有只是为了在整个复杂的地图中描绘自己那一块局部而完美的世界。地理不是一场决斗,而是不同的土地靠在一起。只有给每个人的祖国,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国,那才是每个人的真正正确的地方,而没有其他人的更加真正正确的一个地方。而各个祖国只是在历史上才打仗,而不是在地理上打仗。文学是地理(至少我相信)。
诚然,写作是一场决斗,但是同读者的决斗。而如果你真的还有时间,同评论家决斗。同其他写作的人,从来没有这种决斗。
《毁灭》的土地是我所不在的地方。不过有那种地方。明信片、录像带来了,在那下面喊叫。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地也落入其中,即便你并不愿意如此。例如,我在从东京地铁仕布亚站下来时就迎面碰到了。当我听到〃联合非洲〃的时候,或者当我跟随弗兰克·米来尔一直到哥登姆城去看贝特曼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一些天才的地方,令人激动的地方。难以明白是否只有乔装改扮的迪斯尼乐园,或者由时间的那些地震所重新描绘出来的真正的土地,才是这样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世界全都缩到表面上,而事物的意义都以粉末状态留在所有各地的渣滓上。难以明白。不过仍然有那些土地靠着其他土地,与我的那块土地一起分散在地球表面上。我真的不能看见丑恶或敌人。是地理,不是战争。至少一直到有人决定把我们大家都放进那荒唐的要求以为那里就是真正正确的地方之中的时候。那时候的确会是烦人的。这就是说,我将给我的写作装上乳胶、圆锯和越南色情录像,这样正好伪装一下我,并且逃命。
后来,夜里。到下面小酒店里去。读着莫比·迪克的作品。
/* 38 */
最后的女明星
大家都去斯卡拉歌剧院
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式:鼓、高音喇叭、大幅版面、闪光灯、鞭炮、大字标题。通常的节日。大摆阔气,由裁缝和理发师重新摆弄那些正常配带的小镜子和小珍珠。在人们相当合理地无视存在的一部歌剧格鲁克的《阿尔米德》的快速反击下,媒体显而易见地迷失了方向。意大利学家们和各种人都准备好了要扫描这个神秘剧院的舞台,以便给新领导做一个回声图。围绕这一重大事件,数以百计的人云集在一起,大家准备照一个集体照:天真的音乐迷、橱窗式的面孔、正派的知识分子、寄生虫、不强的强者、正在转悠的意大利人、混进来的德国人、高贵的心、死去的灵魂。粗俗与高雅紧抱着跳起一圈华尔兹舞,在那里高贵与贫贱相混。如果不是现实的现实,那就会是非凡的工程师加达所写的一个故事。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未曾有过的一种文明现象。国家不专注其非常人道的日常事情(美妙与可怕的事情),而停留在管理一个剧院的迷人仪式上。这个剧院熄灭周围的一切而重新点燃过去的片断,低头听着二百一十九年前写的音乐。那个音乐是为一个世界的欢乐而写,而在当时那个世界中,连法国大革命也尚未爆发,广岛的炸弹以及称为电视的那个古怪的伤人地雷都还没有爆炸。如果要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智慧的豪华。人类反抗已经总是令人钦佩甚至是革命的的一种杂技般的证明,就是背负过去这种本能,拒绝忘记和抹去过去:用一个动作就能够做到这样,不被时间所夺走,而成为自己的历史,直到能够记住的地方。从那时至现在,一刻也不少地记着。能够做到这样的那种人的力量永远是伟大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星球上,在这里,有的地方正在重新演奏格鲁克:在现在的科学幻想之中,多么美好的命运。
冷静地想一想,这是一种美好的蠢事。这是一种呼喊复仇的东西。以从现在流露的全部想像,装上了现代这个雷管而等待人名和历史以便爆炸的炸弹,我们因擦亮太祖父的漂亮长沙发而耽搁了时间,才给能够唤起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无数次招待会增加光彩。准确地说,虽然招待会上应邀者寥寥无几,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是全国都关心这个优雅的晚会,并掏自己的口袋来使这一事件获得成功。连一点怀疑都没有,也就是说一点儿也没有怀疑。整个那水晶的丁当声,或者不合时宜的花花公子们他们要庆祝禁止他们未来色欲的那种优雅的无耻行为的恶意卖弄,是同过去的现实而顺利的对话。
冷静地想一想,一个乱结,会使吞下这整个大事变得困难,即便是被消化了而没有大家的鬼脸:仿佛是一种精致的疲劳形式,决定要停留,把歌剧的这种极端荒唐作为不用太多要求即可收到的一种遗产,在暗中怀疑中我们试着想一想,这会是一种没有回路的旅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漂亮剧团逍遥自在的快乐。有人反而会说这会是走向从未有过的激情的一种电动加速;但是,哪怕只是不那么遵守纪律的一种导演就已经使他们灰心丧气,如何做出解释呢?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许多这样的情况之一:在这些情况中,回避问题中心的集体倾向在报复,更喜欢合理地管理已经存在的荒唐情况。在那里思想会有其竞赛的理想场地,漫不经心地玩弄明智,上千名会计师在高级园艺师们的目光下高兴地碎步疾走,这些园艺师们关心的只是没有任何人毁坏草地。就是这样转的。这就决定了一种谨慎的平庸,一种没有生气的思想,一种对事物的近视观点。至少会有人要提醒一下:如果格鲁克本来是这样呼吸的,这样思想的,这样看的,那么我们12月7日在斯卡拉歌剧院就会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 39 */
最后的女明星
橡胶人
①朱利亚诺·阿马托(1938…),意大利前总理译注。他叫Mr。Bean(豆子先生),生活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他的脸像年轻时候的朱利亚诺·阿马托①的那种脸,不过眼睛多一点,特别是:橡胶的。实际上您可以随意地重新描绘他,搬动他捐赠得来的所有一切,包括耳朵。实际上他的耳朵是挂上去的,当他什么都不用再听的时候,他常常把那个东西挂在领带上。运动衫、衬衣、领带(在耳朵上,不过也在其位置上)、连在一起的鞋子。头发经过认真梳理,头路在一边。从表面上看,十分正常。实际上是斯坦利奥、欧利奥、唐老鸭、查洛特、罗莎豹以及托托所有这些人物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于有需要笑到难受包括胃痉挛、泪流满面、令人担心的眼神(亲戚们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人来说,大概是今天在流通中的最好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奇迹。
豆子先生是一个尚属部分秘密的奇迹,因为他不拍电影(他搞五分钟插科打诨),至少在意大利,几乎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你只有两种方式能见到豆子先生:第一种方式:录像带。直至一年前,是进口的,现在带有意大利文字幕,稍稍没那么贵。有人说有七盘在流通,有人则神奇地称有十三盘、十四盘:已经是神秘之物。第二种办法:非常幸运,上飞机去作一小时以上、两小时以内的一次旅行,等待液晶屏幕上停止说明在碰到你会在地上被压扁的情况时应当如何机警地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希望没有时间放整个一部电影,确信最好是比较灵活的东西:豆子先生。我就碰到了(我确认,这是宝瓶星座年),我要说,在那里我明白了那种活的动画片是一个现象。坐在什么也没有的八千米高空,做着《圣经·创世记》一章绝对没有预料到的一件事情(你想想,飞行),这并非是一种舒适的情况。不管你怎么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人的一个位置。并非你觉得真的放松。还有你旁边的人在睡觉,小孩子在哭(对的,惟一有点明智的人),核对表格的经理(目瞪口呆的),盯着机翼害怕得僵直的那个人大概在祈祷。总而言之,当屏幕开始放出图像时,你在看着那些图像。是的,但是用一半神经元,有一定的脱节,这样带有你在吃锡纸小盆里的蘑菇鸡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