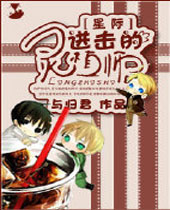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半个小时的鼓掌,意大利万岁。你永远不会知道真实的情况。我想要说,总是有点那种旅游宣传材料的臭味,而只要你有点时间到那里去,看看日本人如何根本不懂我们的音乐剧,而又怎么可能提前一年花大钱买票,以便能在一个夜晚听一位夫人用他们不懂的一种语言发疯,演唱不是他们的音乐,做他们从来不会做的动作,名字也是他们连发音都不会的:《兰梅莫的露齐娅》。有点怀疑。而当你翻开另一页时你想:我想去一次,看看那里究竟情况如何。我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做了。我坐上了喷气式客机,飞过半个世界的上空。打上了领带,票子丢了,又找到了票子,找到了我的座位,第二十一排。露齐娅像上帝一样发疯地唱,以戴维娅的惊人的声音攀登着五线谱,周围,在那半明半暗之中只有日本人。准确数字是两千三百人。他们不是一场噩梦,而是一个谜。相比可能想像的情况不是那么没意思。当我们在西伯利亚上空下面一望无际一万一千米高处颠簸的时候,我问祖宾·梅塔,请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个谜。祖宾·梅塔指挥佛罗伦萨歌剧院乐团和其他许多乐团。他有两三个祖国,他已经把他的这两三个祖国看得足够了,因而可以作为健康的实用主义者。他说:很简单,日本人在他们该有他们的音乐传统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大黑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以某种方式来填补它。于是,在下面就用音乐剧。简单。也是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那个黑洞的简短资料的时候:一位穿着和服的老先生用假嗓子没完没了地唱着那无力的小曲,其简单的伴奏是两位音乐家吃力地用一种小刨子那样的东西,拨弄那忧郁的班卓琴一类的琴弦。实际上,威尔第是另一回事。不过,例如《重归苏莲托》也是个黑洞,那是一种美好的黑洞。于是你可以对你的回答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不是后来,反正你已经在那里,你到了大街上,你可能上了地铁。你在一个叫做石布亚的车站下来,当你出来时,突然你面前是东京。几分钟就足以使你明白,事情应当是复杂得多。
石布亚是一个青年人的城区,在一个没有老年人的城市里,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三十岁就是最老的人。这个城区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那里行人之多使你要排长队过马路。出于无奈,他们在十字路口的对角线上也弄上了白色斑马线。当一个图腾红灯停住了那些汽车的时候,让人通行,柏油马路看不见了,只有那些人。你注意地看看那些人,你在他们所穿的衣服里找到了西方人所发明的那一切的完整标志:大木鞋子和大象腿裤子,球饰和朋克皮革,英国团体式的服装,带有马尔迪尼名字的米兰足球队运动衣,布拉加鞋,迈克·乔丹的耐克鞋,布拉格迷彩服,女裙服和网袜,多德格小帽,两用衫,嬉皮士式淡色小针织衣,约翰·列侬式眼镜,贝纳通西服背心,盖普牌长毛绒休闲服,阿玛尼上衣,托尼亚奇式背心。应有尽有。我没有看见昂贵的老牌爱斯基摩,不过要说一下,这里热得要死。再过一个月也会有那个。不是时髦,不是青年时尚,什么也不是。是一切。有许多欢快的回头客,每个人都有他所喜欢的世界。他们没有个够,他们挤满了商业中心,在那里从洗发水到四季服装,又是应有尽有。而那些回头客还真买。当他们饿了的时候,可以随意地在半个世界的各种饭菜中选择,你只要看一下周围就行了。从汉堡包到烤鸭,又是应有尽有。在那之后,这些回头客就坐在电子游戏机前面消化,在那里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手持大刀的武士,棒球的投球手,复活的F1赛车手艾顿·塞纳,手持机关枪的刽子手,一个足球队的十一名队员。如果他们还想做点什么,那么他们就去找杰克汉斯博士,在那里他们给你穿上一套太空服,把你发射到塞普顿星球上。如果他们有一点时间,他们可以穿过城市,来到一个叫做斯基多梅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那是修筑的一种大棚子,一座八十米高、五百米宽的山,整个被雪所覆盖。你拿来滑车,上到车里,你就滑起来。摄氏零下十度,有着一个pirla或一个上帝的印象,看是在哪个时刻。如果你不会滑雪,那么总是有另一个供回头客去的地方,就是怀德布鲁。这是一个人造环礁岛,有天堂般的海滩,广告画那样的大海。早晨六时通知,不能游泳。实际上大海变化了,起了马利布那种大浪,于是冲浪运动员在那里正好。还有供外国人用的晒黑皮肤的特大灯泡。晚上,他们还有天空中黄昏的效果。你说:好啊,那些是年轻人。好的。那么我们就看看中年人,在〃爱情旅馆〃的那种疯狂故事。
那些〃爱情旅馆〃是日本人去那里做爱的旅馆,不过不是同秘书、秘密情人或搬运工,而是同妻子或正常的未婚妻。正式的说明你在旅游指南里看到的那种通情达理的说明是:有很小的房间,带有隔音,少有的舒适。当人们想要舒服的东西时,开上车,去租一间想要的房子,一个小时,一夜,随便你。如果全部就是那样,那就会是一件只是有点悲惨的事情,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上了〃仕布亚山〃(爱情山),你到那里去看看那些旅馆,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东西。有点粗笨而且往往可怜地假装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之遥。有那种似乎是苏格兰古堡的东西,威尼斯模式的东西,在巴黎的东西。中世纪的小塔。英格兰乡村式的窗户,窗户上有带格子的窗帘,阳台上有花,是塑料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坐在卡萨诺瓦(威尼斯大运河的含糊标志)前面,想起了露齐娅,就是兰梅莫的露齐娅。在那发疯的时刻,一些鬼魂到了她的头上,其中有从未举行的婚礼的那个极为温柔的鬼魂,带着她所爱的男人的那个鬼魂。她开始想像那些细节,她上了仕布亚山,她在其疯狂的小巷中寻找正确的旅馆,在那里关上了现实的无用开关,并戴上了道德现实的头盔。唐尼采蒂飞快地把那个山画了下来,一个陡坡。此时乐队停下了,不行了,一个笛子在正确地坚持伴随露齐娅一直到山顶上,而后一个降E调悬挂在天上。戴维娅在唱着那个降E调,仿佛她的位置永远在那里。而其他所有音符,都是简单的台阶。
事实是,在这里每个人都上他个人自己的山:到了山顶,就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在性爱岭上做爱,或者像一位巴黎模特那样展示服装,或者为意大利足球明星斯基拉奇喝彩,或者听歌剧《茶花女》。一件东西同另一件东西一样,都是一个惟一统一战略的组成部分:构筑人为的和想像的一种人格。你产生怀疑,那个著名的黑洞并不仅仅是音乐、悲惨的班卓琴和八十岁的歌唱者的问题。仿佛黑洞到处都是:它就是这种不合乎道理的爆炸的导火索,当它醒来并喷发出人造的青年回头客和成年滑雪者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它;当它睡在淋巴系统中流淌的静静的职员长河中、即在地铁中的时候,你可以窥测到它。绝对聪明地穿衣服的所有人都一丝不挂,真的是什么都没穿,以至还可以辨认出他们:像哨兵们那样没有个性。尽可能难以觉察:几乎不存在。甚至他们做动作也有天才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之后你好奇地做一个游戏,这就是:你钻进那些人流之一中,戴上墨镜,然后闭上眼睛,继续走路:你在数以百计的人体中走动,而没有一个人碰着你,连擦都不会擦着你一点儿。你该重新张开眼睛,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消失。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大黑洞在行走。于是你产生的看法是简单的:这些都是一个黑洞的儿子。他们带着幻想转向上面,或者由于累了而睡在里面。此外,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讲话的时候在句子里不加主语:我不说(俗气)你也不说(太富于挑衅性)。动词不随主语变位,在一个语言黑洞上翻跟斗。似乎囊括了一切。这是从虚无中逃出的一个精神分裂世界。好极了。但是后来我发生了一件事。东京的一位意大利人对我说:这里没有表达〃虚无〃的一个词,他们要拐着弯说,而只用一个词来说,他们没有。
后来,我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偶然到了阿基哈巴拉:地铁站牌是〃电子城〃。从保险丝到微波天线,那里什么都有,只要你插上一个插头或放进一个电池就能放出音响或影像的东西,都有。你在那个城区散散步,那么你那个关于黑洞的漂亮理论就破灭了。并不容易,但可以努力说明。不过,要到明天。
/* 36 */
最后的女明星
东京(二)
东京阿基哈巴拉,叫做电子城:从东京市中心走两站路,你就到了电子中心。货摊上出售两用插头、电路板、电流计,就像干果那样。商业中心一层又一层,出售能产生影像或音响或音像都有的那些东西。对这类东西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堂。对于想弄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喜爱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的一个人来说,这是可以送给你一种想法的地方。
当你感觉到无论何处转过身你就看到你自己的时候,一切都开始了:到处都有摄像机,为了炫耀产品质量,所有摄像机都开着呢,对着你,把你显示在一个屏幕上:小的,正常的,特别大的。你开始有噩梦。你被数百次放大成各种大小尺寸。如果你试图逃跑的话,你就会落入照相机、复印机、电话、传真机、扫描机中间。所有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复制、重复、倍增。于是你想像在同一时刻让所有、真正的所有这些机器都运作起来,你会感觉到这样一个世界的旋转:这个世界被无限地反复粉碎和爆炸,膨胀成完美复制的一个银河系,发射到数以十亿计的眼睛、耳朵、手和心里。一种令人害怕、甚至还会有所感觉的东西,而且让我们好好地想一想:一个具有某种色欲的游戏,同一种从未有过的、有点隐藏着的娱乐形式有关系。当你明白了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你使劲地想像那种游戏了:突然你感觉到,当你到达成田机场的时候,你就在玩这种游戏了。东京就是那个游戏。你是在一台电子游戏机里面,在那里面一切都已经是经过了爆炸和复制的世界。从头到腿都动过钳子的夫人,从高楼大厦墙上向你投射毒刺或汉堡包的特大屏幕,充斥那些餐馆橱窗的完美的塑料食品,不管你在哪里,都会到达你那里的,全部音乐穿着像埃尔维斯的年轻人和绿头发的那些年轻人,假装在威尼斯的那些旅馆,你进去就给你拍一张照片,而后花七千里拉你就可以修改那张照片,使你变成老人或女人的那种小机器。你在那上面滑雪、用混凝土构筑的那些山,你去那里游泳、用塑料造成的那些小岛,从你面前飞驰而过的意大利维斯帕摩托车,那又不是维斯帕摩托车,而叫做〃吉奥尔诺〃,即〃白天〃,是由本田公司制造的,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更漂亮一点。复制。有区别的世界。巨大的心灵快餐。没有意思:如果你想想,那是有魅力的。如果你想想,那并不是充满最好的东西的一个黑洞的恐怖:是一种更加精细的东西,你甚至已经在书本上学习过它:没有中心的世界,上帝死了,海德格尔①的技术,注释学,软弱的思想;本贾明②的气氛;对阿多尔诺③的表演的迷信:如果你在这里读几年这类东西,那么最终你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实现了这些东西。在这里人们从来不说〃我〃并且没有说〃乌有〃的一个词,你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没有中心但完全迁移到它的边缘轨道上运转的世界。如果在中心有一个黑洞的话,那也已经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所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这里不存在乌有:一切都在旋转,急速地旋转,无需任何支撑点。
①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②瓦尔特·本贾明(1892…1940),德国哲学家译注。
③特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学家译注。如果你能新陈代谢所有这一切,那么你终于也会明白其他更加荒唐的事情。例如日本人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日本人总在那里照相,斗兽场或者红绿灯,总在那里用他们的小照相机:咔嚓。你在欧洲看见他们,简直要使你勃然大怒:有时候他们在还没有看的时候就按下了快门。他们根本就不对一对,似乎他们是马马虎虎照的,他们心里连想都不想要照一张〃漂亮的〃照片。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如果你在东京的电子游戏机场所的卫生间里待一会儿,你几乎要冒明白这种事情的危险。当一个日本人按下照相机快门的时候,他不是在制造一个纪念,或是创造该留住的他个人的一个视角。那个日本人是在拿来一小块世界,把它放在血腥的现代体系中循环:复制它,拯救它。本来也可以让它随波逐流,然而却给了它在现代化中通行的驾驶证,使之成为人工的、更轻的、能在这个时间流上漂浮的东西。最后你还看到了喜爱歌剧的那些日本人的荒唐。你几乎能够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古典音乐是必须以复制的实践作为基础的一个世界:原件不存在,那是写的字,不是声音。它只是在重复这种形式中生存。而歌剧院本身是以更激进的方式进行复制、投影:是它那种方式的电子游戏机。把人的激情拿来,从真情的地平线上把它抢过来,在想像的基础上加以重演:法老、国王、公主、十八世纪的小女仆、巴黎妓女。如果你再加上:像普拉达牌的鞋,或者棒球,遥远的一个世界、一种语言和一种文明搬到这里来了,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想法:日本人会买,他们在一年前就以高价购买了那个歌剧票。他们就这样,像其他许多方式那样,庆祝这个过分的现代化。他们跨上投影的形象而漫游,以此逃出那个死亡的城市。那城市过去曾是真实的所在,如今已是被遗弃的无用的城区。
这样我看见他们进入混凝土和木头构筑的大剧院里去看歌剧《兰梅莫的露齐娅》,他们穿着朴素,就像去看一场马术晚会一样。有一个声音劝他们不要拍照,如果有人敢拍照,就要遭到谴责。后来大幕升起,我看见他们认真地看着数世纪前一个苏格兰姑娘被迫同她不爱的一个男人结婚,于是新婚之夜在床上杀死他的故事。他们看见她发疯,看见她唱着温柔的音符和惊慌失措的音符。最后他们看见一个男人在她的尸体上自杀,因为如果不能一起生,你总可以想像能一起死。场景是漂亮的(格拉汉姆·韦克所设计),有祖宾·梅塔指挥的佛罗伦萨歌剧院乐队和舞台上无可挑剔的声音(其中有最好的马里埃拉·戴维亚和文琴佐·拉斯科拉)。日本人鼓掌很长时间,没有爆发在类似场合中神话般的狂热欢呼,但是回到家里那脸上的记忆并不容易抖掉。他们很少喊叫,但是无限平静地鼓掌。最后他们用小手互相道别,像在立交桥上的那些人那样,像看见一艘轮船起航的那些人那样。有点令人可笑,然而,如果你真的没有淹没在玩世不恭之中的那种灵魂,那么最终会使你甚至有点儿激动。
外面,门口在下雨。有一个台风正在到来,大家都希望改变主意而到中国去。夜雨,数以百计的灯光招牌,到处都是像小虫子一样的人。充满BladeRunner。你永远不会明白你是否能真正喜爱这样一个世界。它具有正在到来的未来气氛,然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