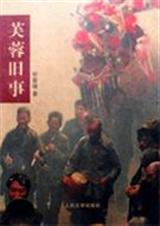西宫旧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襄见她要离开,一把拉住她的衣袖道:“姐姐,你别走。” 嫣红抽回手,轻啐一声笑道:“你还真会磨人,等我把针线活拿过来陪你。”随即从外间端了一个盛满各色丝线的盒子进来坐下。
沈襄见盒子的最上面放着一个做了一半的荷包,“咦”了一声探起身,伸长脖子去看。那个荷包的做工异常精致,深蓝色的缎面上,并未象坊间流行的那样绣着花鸟虫鱼,而是用白色的丝线绣了两句诗:“借问梅花何处落,从风一夜满关山。”他看了一眼嫣红,问道:“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戌楼间。原来姐姐也喜欢高适的诗。”嫣红的脸微微一红:“这是高适的诗么?我并不知道,只是在公子练字的时候看到,很喜欢这两句。”
听到公子两字,沈襄忽然失了兴致,立刻想起自己的处境,躺回去闭上眼睛。嫣红以为他累了,也不再说话,房间内顿时寂然无声,只能偶尔听到木炭燃烧时的噼啪声。
这个情景,让沈襄既熟悉又陌生。以前在家时,母亲也是这样,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守着他兄弟三人读书。从他兄弟三人入狱,已经有半年了,一直没有母亲的消息。想起冤死的父亲和屈死的兄弟,心里又酸又苦,两行眼泪悄悄从眼角滚落。
父亲在家书中曾评价过曹懿“聪敏睿达,少年天才,惜乎攀附权贵,大节已亏。”他这样处心积虑地安置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细细回想那天情景,却越想越糊涂,索性撂开了,自己已经落到这样的田地,还能坏到哪儿去?最坏也不过一个死字。这么想着,心里一宽,竟觉得肚子咕咕叫起来。
周彦回到书房,见曹懿正和方先生坐着说话,便蹑脚进去。曹懿看见了只微微点头,示意他坐下,仍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倭寇一旦来犯,往往连舰数百,蔽海而至,纵横来往,如入无人之境。浙东西、江南北、福建、山东、广东,东南七省,滨海数千里,竟同时告警。去年虽有川兵破贼周浦,俞大猷杀敌海上的战绩,狠狠打击了倭寇的气焰,可这水来土挡、兵来将挡的办法,终不是长久之计。”
方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颌下几绺长须,颇有些仙风道骨。他是老候爷十几年的朋友,也是曹懿的启蒙恩师,虽然满腹经纶,却一直没有出仕。曹懿一向以师礼待他,府中上下皆称为“先生”。
方先生用火筷子拨着火盆里的炭,半天没有说话。沉吟了良久方开口道:“倭寇之患之所以数十年连绵不绝,并非全因为倭寇彪悍贪婪,我朝亦有几点心腹之患,这几点祸端不除,想要海防平靖,实在是难于登天。”他伸出手掌,每说一条便搬下一个指头,“第一,卫所军的兵士均来自北方,不惯水战;南方沟渠纵横,不利驱逐,旱地的阵法竟无一可用;第二,倭患之烈,始于禁海,如果一意痛剿,激起贼寇死斗之心,贼更难平;第三,沿海祸患虽称倭寇,其实真正倭人只占十之二三。本地海盗为其首领,间谍探子密布境内,敌在暗,我在明;第四,倭寇侵害的是山东、浙江、江南、福建诸省,本该同仇敌忾,共同御敌,可惜彼此之间却相互戒备,甚至互相拆台。”
曹懿惊异地说道:“先生真是运筹于千里之外,一语切中要害。我在浙江这一年,冷眼旁观,先生所说的四条,竟是一条不差。”他低头吹去茶碗中的浮沫,长叹一声道:“这些事一旦要改变起来,颇耗费心力,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奏效。去年还仰仗着赵文华在严嵩那里斡旋,十月他因罪去职,兵部户部忽然间多了诸多牵制,百般刁难。军饷钱粮稍有迟误,那些总兵、参将就鼓噪不已。为讨皇上高兴,前线又不能断了捷报。这个军务提督,竟是个几头受气的角色。”
方先生看了看曹懿苍白疲倦的面孔,一脸忧色道:“公子这次回京,也有十来天了,我旁边瞧着,进宫见驾,兵部述职,会见官员,还要批复浙江转来的公文,竟无一刻得闲,每天睡不了几个时辰。我估摸着在浙江,情景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身子秉性就弱,又有个旧病根儿,却这么不吝惜自己。”
曹懿苦笑一声垂下眼睛,眼圈有点微微泛红。这一年在浙江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从浙江巡抚到浙直总督,皆是十几年宦海里滚出来的老油条,哪里会把这个资历甚浅的年轻钦差看在眼里。不过是看着严嵩的面子,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虚与委蛇,暗地里不知做了多少手脚。而六部官员,又有哪个是省油的灯,一个打点不到,关键时候他就能抽你的底火。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维持到今天的局面。
方先生这时才发现周彦站在旁边,遂起身拍拍他的肩膀道:“周彦来了,怎么不坐下说话?”
周彦咧嘴一笑:“先生,您没瞧见,公子如今见我还是板着脸,我还是小心点好。还有,您老若是真的心疼我,千万甭让我坐。”方先生这才想起那十板子的事,不禁失笑。
曹懿却没有笑,只是望着手里的茶杯出了会神,方才转头问周彦:“他醒了吗?看着怎么样?”
周彦忙站直了正一正脸色,垂手肃然答道:“气色还好。就是一时半会的,他心里恐怕还拧不过这个劲儿。”
曹懿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唇边忍不住掠过一丝微笑,很快又敛去笑容问道:“见到沈夫人了?”
“是,我在城南租了一套小院子,已经帮着沈夫人搬过去了。沈夫人让我带话,她明白公子的一番苦心,母子相见,不急在这一时。”
“人带来了?”
周彦指指外面:“早来了,在后面候着呢。”
曹懿这才点点头,对方先生说道:“沈襄才十三岁,一夜之间遭遇剧变,先没了父亲,又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死在杖下,他还能把持住,神智纹丝不乱,确实不是个一般的孩子。”
方先生摇摇头叹道:“沈鍊死后,一手操办此案的两个严党亲信,宣府巡按御史路楷迁升五品卿寺,宣府总督杨顺一子荫封锦衣卫千户。已经得尽了好处,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的儿子?”
曹懿目光一冷:“当初我也想不明白。前日与人闲谈,才解了谜团。说起这个杨顺,竟是因为路楷提升,心中不满,认为自己没有讨得严世藩足够的欢心,所以才演了杖毙这出戏。如今杨某已经进京待选了。有人看着眼红,又盯上了沈襄,打算原样炮制。”
周彦忍不住插嘴道:“那……收留沈襄,会不会得罪了小丞相?”
曹懿看看他,眼中尽是一片揶揄之色,“你怕了?逞强出头做英雄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怕?”
周彦尴尬地低头笑笑,没有言语。
“放心,这不是小丞相的手笔,只是有人想讨好他。可惜这个人心智不够,如今弄得处处皆是破绽,哪里还敢自己往枪头上撞,等着那帮御史们参他?”
方先生诧异地问:“什么是小丞相?你们两个说话越来越古怪。”
周彦嬉皮笑脸地说道:“先生难道没有听说过,严太师每回入值西内,几乎数日不出,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皇上用来斋醮的青词。所有朝务都交给了严世藩。六部有事请裁,太师均对之‘何不与小儿商议”或者‘待我与东楼商议’。如今是严氏父子双双名震天下,京师才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
方先生大笑道:“大丞相小丞相?这些人也真想的出来。”
“周彦说话总是这么刻薄不饶人。严世藩为人虽然贪得无厌,可也是天资聪颖,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起草的青词,辞藻典雅端丽。任何公文均可过目不忘。平日皇上批出来的手谕,语多艰涩,别人不知道在说什么,只有他揣摩得真切,酌情奏答,竟然条条附和上意。严嵩父子能够十几年恩宠不衰,并不是一味只靠奴颜媚上。”曹懿说着起身扶起方先生:“先生一起去吧,您也见识见识这孩子的一张利嘴。”
沈襄正倚着枕头坐着,嫣红端了碗银耳羹,用小匙一口一口喂他。见曹懿、方先生和周彦陆续进来,连忙放下碗站了起来。
方先生看了看沈襄的脸色,又扶起左手切了切脉,含笑道:“果然是年轻,恢复得真快。”曹懿在他额头上试试温度,说道:“还好,那些伤实在是凶险,幸亏熬过来了。”
沈襄却一把拨开他的手,“哼”了一声闭上眼睛,曹懿并未在意,只笑了笑对周彦说:“你把小桃带进来。”沈襄闻言霍地睁开眼睛,果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怯生生地走进来,竟然真的是服侍母亲的婢女小桃。他几乎是光着脚跳下床,不可置信地叫了一声:“小桃?”
小桃浑身哆嗦着抬起头,看见沈襄立在她的面前,双目中立刻储满了眼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抱着他的腿放声痛哭:“二少爷,您真的还活着……”
沈襄弯腰扶着她,激动得几乎口齿不清:“小桃,你怎么会在这儿?夫人呢?”小桃哭得几乎说不出话:“夫人……得到大少爷和三少爷的死讯,就病倒了,又听说你也……夫人她……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沈襄双腿一软坐倒在地,目光发直,眼睛却干干的没有一滴眼泪。
曹懿向周彦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走到外间。曹懿简短地吩咐道:“这个丫头年纪太小了,把她留下来服侍沈襄,沈夫人那里另派几个妥当人过去伺候。从今天起,沈襄这个名字要彻底消失,就改名――端砚吧,让他去书房伺候笔墨。”
周彦咧咧嘴,屋里的哭声让他心里沉重,想笑却没有笑出来:“又把个红炭团儿塞给我,这小子天生就是一根犟筋,让他改名做家仆?”他朝天翻了个白眼,“兄弟,你让我生个孩子可能还容易些。”
一向四平八稳的曹懿,忽然有些急躁:“他根本就不信任我,否则还用劳你的驾?一个大活人藏在府里,这是唯一保全他的办法。”
周彦急忙举起双手,一脸无奈状:“好,我去说我去说,你别上火,我不想一个月挨两次板子。”
曹懿忍住笑转身下楼,忽然想起一事,又停下脚步:“噢,对了,昨天严府送来帖子,严老太太二月十三八十大寿。南书房还存着一幅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麻烦你取了亲自去趟严府,说我过完正月启程去浙江,不能亲自拜寿,聊表存心。”
方先生从里面慢慢踱出来,听到最后一句话,便道:“你这次回来,至今还没登过严府的门,不怕那边记恨?”
曹懿听了冷笑一声:“严府门外每天的轿子能排出二里地,溜须拍马的人,不缺我一个。他举荐我做这个提督钦差,不过是念着爹当年弹劾过仇鸾的那点情分,拿我做个棋子,去挤兑赵文华。我办事得力,他在皇上跟前也面上有光。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彼此敷衍着过得去,江浙的事他不从中作梗也就罢了。难道让我去学仇鸾和赵文华,赶着严嵩叫爹?”
仇鸾早年间是严嵩的义子,靠着严嵩的提携一路爬到京营大将军的位置,开始与严嵩争宠,变为严嵩的政敌。曹老候爷曾弹劾仇鸾渎职养寇,导致北部边境屡遭东蒙古鞑靼部落的骚扰。仇鸾病死后,通虏纳贿案发,嘉靖震怒之下,仇鸾被剖棺戮尸。
赵文华是曹懿的前任,也被严嵩认为义子。在浙期间,因“柘林大捷”和浙直总督张经争功不成,上疏弹劾张经,说张经身为闽人,与海寇多属同乡,所以徇情不发,养寇失机。此案最终共株连一百多人,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总兵汤克宽等九人以通倭冒功之罪,尽拟处死,严嵩捎带着把弹劾自己的兵部武选司杨继盛也纳入此案,一并西市处斩。
赵文华因抗倭有功,升任工部尚书,并加封太子少保。圣眷之下,开始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严嵩心里便存了芥蒂要拔掉这颗眼中钉,恰好此时松江大败的消息传入北京。原来张经死后,继任总督杨宜能力威望远逊张经,沿海的倭害因此更加猖獗,这一仗指挥以下的将官战死20余人,士兵死了上千人。嘉靖揽疏大怒,严嵩趁机推荐向嘉靖推荐兵部员外郎曹懿,自幼颇娴军事,可提督浙闽军务,再下江南,嘉靖对此并无异议,在票拟上朱批了同意二字。
曹懿赴任不过半年,倭寇的嚣张气焰略略平息,宫中便传出中旨,命赵文华督建正阳门楼,限两日完工。结果限期一到,门楼只建成一半。赵文华随即被削职为民,回籍休养。
方先生见他又提起这段旧事,一时也是无言。曹懿一脸愠怒,竟拂袖而去。周彦冲他做了个鬼脸,笑道:“先生,这些天公子吃了火药一样,您也离他远点,少招惹为妙。外头的话,早已传得不堪入耳,为这个他几次气得饭都吃不下。”
方先生望着曹懿的背影,微微叹了口气。
东花厅原是一座建在水面上的抱厦。老候爷在世时,只是用来夏季邻水垂钓,取其凉意,后来改做曹懿处理公务的地方。这间东书房几乎是候府的禁地,除了周彦和方先生可以自由出入,其余家人未经允许不得轻易踏入一步。书房内的布置很简单,最醒目的装饰,是西墙上挂着的一幅东南海域图。
曹懿对着这副地图,皱着眉头坐了一下午,几乎没有改变过姿势。直到大门负责司阍的家人在门外唤了一声: “公子。”他才惊觉抬头,发现窗外已是暮色四合。也许是坐得太久,站起身时竟然一阵天旋地转,扶着桌子好一阵才站稳,扬声问道:“什么事?”
“徐大人来访。”
曹懿手中的笔几乎失手落地,一步跨出房间,问道:“谁?你说谁?”
“徐阶徐太傅。”
曹懿定定神,随即平静地吩咐道:“带徐大人到客厅,我换了衣服就过去。”家人答应着去了。
他在暮色里静静坐了一会儿,嘴角忽然溢出一丝笑意,那笑意越扩越大,却充满了嘲讽之意。
徐阶负手站在客厅的一副中堂前,正看得出神。他身上还穿着全套的朝服,显然刚从宫里出来,虽然个子不高,但面目疏朗清秀,浑身上下显得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幅中堂是一张大写意的泼墨山水,崇山峻岭间隐现着迤逦的万里长城,旁边一副对联,却是一笔酣畅淋漓的狂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听到脚步声,他回头笑道:“小侯爷这笔字,秀丽中颇见风骨,银钩铁划,竟隐隐带了风雷之声。”曹懿笑着拱手:“徐世伯谬赞了。这是小侄在大同闲来无事写着自娱,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两人叙了宾主坐下,曹懿从家人手中接过茶盏亲自奉上,笑道:“早就说到府上拜望世伯,可是事务缠身,实在匀不出时间。请世伯多体谅些小侄。”
徐阶好奇地打量着曹懿,见他穿了一件淡青色的银鼠夹袍,满头黑发只用一顶细银缂丝冠束在头顶,握着茶杯的手指修长白皙,皮肤细腻得近乎透明。想起来自前线的那些传说,实在难以想象这样柔弱的一个人,如何冒着流矢箭雨,在千军万马前发号施令。
两人寒暄了一阵边塞风物,提到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