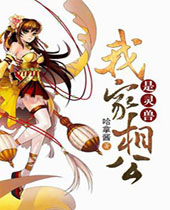邓丽君私家相册-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泪,但没说为什么,我猜因为是客串,只有几分钟,所以就随便吧。 但在这部剧中,邓丽君真是非常投入,她很喜欢这个角色。在1978年的《电视周刊》中有一段关于这个剧的专访,提到邓丽君在最后一段化上京剧青衣的装时,自己觉得太漂亮,都不想将头套卸下来了,但是戴久了头很痛,才了解唱京剧的人是多么辛苦。当时在剧中和邓丽君演对手戏千金大小姐的李蕙蕙早在1967年就是邓丽君主唱的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的童星女主角。算是很有缘。 后据一位非常了解这部剧的情况的Antonio称,这部邓丽君在1978年所主演的“台视”剧场《天涯常念旧时情》,曾回放于1997年。
第三部分: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5)
当时由台湾名作家张曼娟作引言,介绍“台视”剧场早期20世纪70至80年代经典戏剧。其中不乏台湾现在当红巨星。第一集就是邓所主演的戏剧。当时引起不少回响。因为堪称是邓第一部电视剧。那首主题歌《想你想断肠》,是取自闽南语名曲《补破网》,很特别的是邓丽君将这首歌曲唱成国语歌。因为当时台湾剧场是采用单机作业,所以整出剧的步调尤其是运镜显得有些迟缓。剧情是专为邓丽君量身打造的。听说邓揣摩剧中角色很下苦功。据报道她紧张得吃不下任何东西。心疼的邓妈妈让她喝了些牛奶补充体力!邓的执著可见一斑。让观众最印象深刻的是邓的台步走得很特别,有点脱离不出舞台的台步感觉。邓的演技很好,可能她的特质就是如此,尤其她的声音听起来温柔婉约。剧中一幕是邓吟词怀人(家教先生),她吟读的就是《淡淡幽情》第七首李后主的《乌夜啼》!不过不同的是“留人醉”改成了“相留醉”(事实上就是“相留醉”是正确的)。邓丽君穿凤仙装的样子当时不知迷煞多少青年才俊。她的笑容也很特别。1992年她接受“华视”专访时,当记者访问说大陆许多青年都很喜欢传唱邓的歌,邓掩口一笑,风情万种。不管如何,看她笑就是很迷人的感觉。 1978年,邓丽君全家人在台北的合影,站在后排的邓家四个兄弟,真是各个不同。 邓父曾对家人当笑话说,邓家有四个壮丁,只有一个独生女,将来女儿出嫁时,正好兄弟四人,一人一边,帮她抬花轿。只是邓丽君终生没有结婚,让四个兄弟没有了用武之地。 P116…117 1978年,邓丽君在香港利舞台演出时,主办方制作的海报。 香港为邓丽君组织的一次“邓丽君金唱片竞猜游戏”,她在港获奖无数,而金唱片奖的获得也是创纪录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已经在日本走红,事业成绩更加辉煌,不过她并没有放弃在台湾或者香港、东南亚等地的音乐市场,成为一个“国际巨星”的梦想渐次清晰,唱片出版的规划也做得更加细心,除了固定推出的国语、日语专辑之外,1980年、1981年两年时间里,邓丽君努力学习马来语、粤语,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连续推出以前从来未曾灌唱过的马来语、粤语专辑。这两张是她在当时台北最好的摄影棚国陆影像拍摄的宣传照。 在日本演出的照片,表演吹奏横笛。 日本的唱片业相当发达,每年的新人数以千计,能够获得新人奖的只有五六个罢了,而能够生存下来的则更少了。因此,每个新人都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空港》大卖使邓丽君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在日本初期的辛苦她开始就有预料,而她的勤奋也感染了身边很多同事或朋友。 在日本演出中,手持一枝鲜花。 翁倩玉的照片,邓丽君在日本发展的时期与之多有交往,翁是早期去往日本的艺人,也是早期的国语歌手,曾主演过多部影片。她撰文回忆说: 第一次见到邓丽君的时候是她在台湾刚出道后,她重唱我的国语歌《再见十七岁》,两个人同时想唱红它。回想起来,和邓丽君也往来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之后有段空白的时间,知道她在日本出道还吓了一跳。 应该是1987年吧,在东京音乐祭亚洲日的庆祝派对上见面时,聊到彼此发声训练方式的话题时,还要了她使用发声训练用的录音带。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吧。那卷录音带我在带回去的路上丢掉了,跟她在电话里提到此事她还说马上补寄给我…… 她的死讯在电视报道前就从香港朋友的电话中知道了。明明最后一次见面时,她的脸色还很好啊!令人无法相信,甚至无言以对。 再也没有人有那样甜美的声音了,真的没有了,我想能唱出那样的歌声是要经历过相当的人生历练才能做得到。压抑自己再由自己摘取燃烧中恋爱的花朵。在累积这样的历练后才能唱出那样的歌吧。她真是一个认真的专心的有想法的人。 晚年我的朋友在新加坡见到她时,她还似乎相当欢喜的样子。是在抵抗疾病的魔掌吧!要再一次的尽力让自己保持活力的状态是需要相当的能量的啊。在病魔和自己的健康状态之间应该相当的困扰吧。 可称她为架起亚洲沟通桥梁,共同奋斗过来的战友、或者称之为同志吧……可惜我已经失去这样的伙伴了。 —翁倩玉《痛失同志》 日本圣诞演唱会前与母亲的合影,母女间的装扮有点类似。这对母女有诸多来此一游式的图片为证,她们共同走过了人生中的跌宕起伏与喜悦。 1977年5月,在日本新桥TV演唱会中。邓丽君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抱着礼物,喜笑颜开,她在东京举行的”何处是故乡“歌曲大赛中,夺得第一名。 邓丽君到了日本发展后,无论唱歌技巧还是外型都有不少变化,这当然是签约公司包装和她本人努力的结果。而在其后对在日本的演艺阶段的回忆中,邓丽君亲口谈到自己在日本期间努力保持着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她说:“我在日本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形象,所以演唱会或电视演出的时候,歌迷都会特别要我唱两首中文歌的。”像《何日君再来》《泪的小雨》《高山青》等歌是她常唱的曲目。 1977年8月26日,在日本川井夜总会里演唱。 邓丽君的父亲有着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权威和严肃,在进军日本歌坛的时候,邓父不能理解已经在东南亚成功了的邓丽君为何进军日本时还要从头做起,并以“泰丽莎·邓”为其在日本的艺名。
第三部分: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6)
邓丽君的弟弟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透露了这其中的细节: 邓:日本公司是在香港的歌舞厅发现到(她)的,所以就跟她谈到日本发展,那时候已经是20岁的时候。 记者:她当时有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过程,去不去日本发展? 邓:去日本,我父亲当时坚决反对。我父亲觉得,她在台湾、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了,那去日本,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母亲也怕日本人,因为以前抗战的时候,逃日本都来不及,那她是自己想去闯一闯。所以后来就答应了她,我母亲也愿意陪她,那我父亲也无所谓了,反正你们母女俩决定的,不要后悔,所以大致过程是这个样子。 记者:当时日本唱片公司为什么要来这边找中文的歌手? 邓:也不是很刻意要找中文歌手,因为那个时候,她们公司在香港叫宝丽金,在日本叫宝丽多,所以都是一个公司,那等于说把香港,她那时候已经加入宝丽金里面,把香港的歌手带到日本,再去发片,这样子。 记者:她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台湾对日语的节目,不许在电视上播放,广播里可能也不让播放了。 邓:对,广播,广播不清楚,尤其电视,不准唱日本歌。 记者:那她去日本发展,会不会影响她在台湾的发展,会吗,在那个时候? 邓:还好,反而就是去日本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回台湾,所以她那个时候知名度还都没有怎么受影响。反而就是觉得变成旅日红星。 1977年6月,在日本原宿家中的休闲照。她与照片上那位纯朴的小姑娘形象形同天壤,只是图片上的邓丽君望着现实中的邓丽君时,恍若两人。 照片中的她戴着头巾,但可别以为这仅是简单的饰物而已,其实,这也是为了挡住她前额的伤口才扎上去的。 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一直头痛起来,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就医才发现,她前额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邓丽君不得不动了手术,在前额上缝了十针。 那段时间,邓丽君常戴头巾,她说:“并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遮盖住伤痕。” 1977年11月,在日本原宿的家居照片。 在东京一家夜总会的演出现场。邓丽君已融入到当地的氛围中。 1977年在东京银座的演唱会上。邓丽君的装饰极具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时尚气质。 1977年10月30日,在东京为新曲宣传,与世运冠军选手举行“邓丽君杯”自行车比赛。她的身后是一群骑着单车的小朋友,装扮也很像个学生。 当时的经纪公司为了塑造她的清纯形象,要求她必须留长发、穿有袖子的衣服,这张照片上的形象就很契合当时的包装思路。不过,过了一些时间之后,邓丽君长发留腻了,她亲自动手把头发剪短了,公司看了她自己设计的新造型,也觉得不错,就接受了。 为了演出效果,邓丽君曾多次在电视节目中以各种不同造型出现,如和服、武士服装扮相等。当时日本走玉女路线的歌手很多,而年轻时的邓丽君,长相甜美,有天生的清纯少女形象。为了和另一些歌手以做区别,经纪公司转而将她包装为成熟、哀怨的新形象,她的唱腔也随之做了改变。P126…127 1977年邓丽君与母亲,摄于东京原宿自宅楼下的咖啡座。邓丽君的母亲是个朴实的中国女人。邓丽君曾说过:“我唱歌的时候喜欢妈妈在现场,这样我会比较安心,她总是在我心里。” 初到日本,最困难的就是语言问题,不过她的语言天赋派上了用场,她曾经说:“日语,没有这么困难,也许它的发音比较简单。其实我还不会讲日语的时候就开始录日语唱片了,只要发音窍门抓对了,其实没有那么难。” 她的弟弟邓长禧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曾回忆了她初到日本时的情形,以及她是怎样克服语言障碍的。 记者:日语呢,她去之前一点都不会吧? 邓:一点都不会,去那边才学的。 记者:但她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 邓:嗯,这个我也蛮佩服的。 记者:那她唱日本歌的时候,是日语基本会了以后才开始唱日本歌,还是一开始就是死记那个发音? 邓:死记,就是用英文去拼,拼那个音。所以你看她很多以前的那个笔记,她把不好念的地方,就用英文去注解,那个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咬,很辛苦的。 记者:那唱一首歌还好办,如果是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要唱很多首歌,她都是这么记下来? 邓:后来就背熟一首,那一首就没问题了,所以就是一直在背新的歌,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每一次唱还要再去背,她就等于把那首歌熟练了。 记者:在日本发片,一开始就很顺利吗? 邓:没有,第一年公司还检讨,说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出了两张片,都不卖钱,后来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的那个人,他坚持说,再给一次机会,再出一张片,所以等那张出来才等于得到一个肯定。 记者:她不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排行榜上是排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上就卖,以下就不卖了? 邓:根本就没有入排行榜,日本新人很多,日本新人一年大概有上千人在角逐,然后她那时候发片还不是大碟,他们叫single,就是一张单曲,先卖单曲,单曲都卖得不好,然后就不可能出大碟,所以到第三张的时候,那一张单曲叫《空港》,《空港》那张一下就蹿到排行榜上,后来再出大碟,然后她那一首歌也得到当年日本的新人……等于是最佳新人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她等于是奠定了她在日本的一个基础。在台湾所唱的歌曲,不少译自日本,因此她在旋律和风格方面都很熟悉。但是日文发音就可整惨了她,她说:“注音符号、国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部用上了。” 邓丽君1977年参加日本一家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她在日本期间经受了全面的明星模式训练。
第三部分: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无端更渡桑干水:北上的列岛(7)
香港的另一个音乐制作人张文新是这样评价她进军日本的:“我觉得她唱歌的技巧进步许多,在日本可能吃了不少苦,不过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她可以唱得非常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她可说是以国语介绍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风、感性与传统的中国式唱法已在她的体内合而为一。这在香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的确,邓丽君当初与宝丽金公司签约的时候,她的恩师常荫椿教授就曾经嘱咐她不要忘记了自己是个中国人,也不要丢掉自己的民族特色,虽然其间,老师曾有误会于她,写信指责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但是时隔多年,当常荫椿教授从报上得知邓丽君在日本演唱的许多歌曲都是中国的歌词和曲调,也就消除了心中的不快。 身着有浓郁中国风情的服装接受日本电视台的采访。 在一次演唱会上,邓丽君偶然穿起了一身旗袍,她玲珑有致的身材被衬托得恰到好处,这个装扮受到了歌迷热烈的追捧,而她修长的腿也一览无遗。此后,邓丽君便经常身穿旗袍亮相,起初,这些旗袍都是由邓父由台北送至东京,后来,有一位在日航任职的歌迷义务为她完成了这些服装的运输任务。 其实,邓丽君在日本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是1973年的《无论今宵或明天》。这张专辑与熟悉的“邓丽君式唱法”有所不同,她穿上短短的迷你裙,留了长发,一边唱歌还要一边摆着日本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一点也不适合她自身的个性和特征,因此只打进排行榜第75名,但当时的销售量也有十多万张。 《邓丽君之梦》一书中记载了曾经与邓丽君共事的姚厚笙对她这次奔赴日本再发展的决定的评价:“日本音乐当时比台湾的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台湾的乐队只有简单的吉他、鼓、键盘等乐器,日本却有大型的乐团,乐器的种类繁多。光这一点,音乐就丰富了许多。唱歌有时候还有管弦乐团伴奏。她的声音之所以更放,唱歌的感情之所以更丰富,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在新加坡演出的照片。 1977年,24岁的邓丽君在日本上电视综艺节目,做艺妓秀。 为配合唱片公司的宣传,提升人气,邓丽君在电视台的这档综艺节目中不但上台作了日本传统的艺妓表演,还向人们展示了艺妓化装的全过程。 这是富士电视台的节目,表演前,邓丽君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化装。邓丽君对日本的文化习俗也很有兴趣,她说,“我去日本的时候是1974年,虽然没有期望能大红大紫,但是希望能学到一些不同的文化和另一种语言。” 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节目艺妓秀之后,邓丽君以日本浪人造型再次登场。 1977年邓丽君出席东京”新宿歌谣祭”。其实,邓丽君是在1975年获取日本“第十八届唱片大赏”和“新宿歌谣祭”的新人奖的。 在日本的前四五年时间里,邓丽君平均每个月都要办一场个人演唱会,在1小时45分钟的演唱中,必须要准备3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