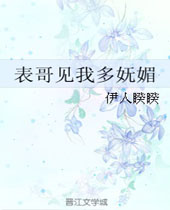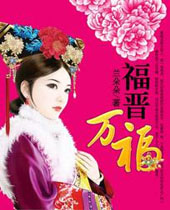表哥万福-第3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沈姑姑也是一愣,半晌才道:“北境乃是苦寒之地,韶懿郡主……”
太后娘娘又叹了一声:“既封从懿,必承其德,她当得起。”
沈姑姑垂头听着,没说话。
太后娘娘却心念微动:“瑞雪兆丰年,去岁冬天,整个北方没下过几场雪,眼看已经到了二月,天气还冷得跟冰窖似的,看来今年又是一个灾荒年。”
沈姑姑轻声道:“您已经尽力了。”
皇上服食丹药,致丹毒於体,病在宫里,已经许久不理朝政,太后娘娘为防走漏了风声,以致朝纲不稳,命人封了殿门,兰妃娘娘想让二皇子从御书房,走向前朝辅政,趁机揽权,与太后娘娘达成了共识,也对此事秘而不宣。
眼下皇上宫里,是由兰妃娘娘把持。
她掌控后宫多年,在宫中势力根深蒂固,就连徐贵妃也没察觉出端倪来,只顾着联同徐国公府,在朝中拉帮结派。
太后娘娘看着折子,沉思良久问:“皇上的龙体可好些?”
沈姑姑心下一紧:“兰妃娘娘的人说,还是老样子。”
那就是没有起色,太后娘娘目光闪烁不定,半晌才道:“你将韶懿的折子,送去内阁。”
韶懿郡主的折子里,也只是在闲话家常,叫人挑不出错来,可有心人瞧了,难免就会生出一些旁的心思来。
京三省各地流民暴乱,频发不止,连官府也镇压不住。
朝廷若不能尽快想出对策,越来越多的流民聚众一起,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甚至还会引发大范围暴乱,危及社稷。
可国库空虚,朝臣们也是束手无策。
眼下北境还有余力收容流民,内阁哪还能坐得住,当下就召集群臣们一起议事。
内阁因为虞宗慎丁忧去职,闹腾得十分厉害,但户部仍然掌控在虞宗慎手中。
为了巩固保皇党在内阁的话语权,保皇党这一脉发动人脉,将虞氏嫡脉的一位老臣送进了内阁。
虞氏族在内阁的地位不可动摇。
虞阁老正老神在在地听着,朝臣们就有关流民的安置问题争论不休。
等双方口沫横飞,争得脸红脖子粗,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齐齐看向了虞阁老:“虞阁老意下如何?”
虞阁老收到了虞幼窈的信,对北境的情况,了解得比旁人多,心有成算,面对众多的诘问,自然也不慌不忙。
他出声问:“韶懿郡主为什么要去北境?”
都察院都御史齐大人,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中有了猜测:“折子上提过了,是因为武穆王要在北境受灾较轻的地区,推广番薯种植,缓解旱情,因番薯是韶懿郡主试种成功,关系北境数以千万百姓们的生存,武穆王请了韶懿郡主相助。”
虞老阁再问:“武穆王为什么胆敢收容大批流民?”
齐大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那是因为东北三省受旱较轻,并不影响番薯种植,番薯贱活,耐干耐脊,还饱腹,只要在东北三省推广种植,有了番薯,武穆王自然不担心,流民们没有食物。”
两人你来我往,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
虞阁老笑了:“这不就结了?”
“结了?”朝臣们面面相觎。
虞阁老干脆把话说明白了:“北方大部分地区都遭了旱,田地里旱着,不能种庄稼,东北三省受灾轻,正好武穆王要推广番薯种植,那就把流民迁去种番薯,武穆王手握重兵,流民们有武穆王震着,也不敢乱来。”
朝臣们顿时无语了,有些心动,但又畏惧武穆王之威,担心把这个大麻烦扔给了武穆王,武穆王会不乐意。
“这、这样不大好吧,北境是在武穆王辖下,他收容北境的流民,也能说得过去,若是把其他地区的灾民也弄过去,几百万张嘴等着吃饭,番薯这还没影呢,怕不是要把军晌都吃空了。”
“武穆王没有义务接收除北境以外地方的流民,他若是拒绝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啊”
“对啊,武穆王也不是好相与的,还是不要去触他的霉头……”
“这、万一惹恼了武穆王,就不好收场了……”
“……”
第801章 龙游于海
把流民迁到东北三省去,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既能安置流民,给流民一条活路,又能解决一个祸患,将流民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武穆王。
但问题是!
武穆王也不傻啊。
经过山东平叛,周厉王一案,武穆定北王已然在朝中立威显能,尤其是内阁,对他尤其忌惮。
虞阁老一脸恨铁不成钢:“我说你们一个个,平常看着挺精明的,可到了大事上,怎么就犯起糊涂来了?你们想想啊,大周朝初立之际,高祖皇帝在辽东一带,下设了辽东都司军镇,言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并且颁发了一系列强边御外的国策,还将大批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迁往了北境。”
朝臣们渐渐回过味来。
齐大人更是一激动,猛拍了一下大腿:“对啊,北境地广人稀,迁移流民,发展人口,进而提高生产力,也符合强边御外的国策,既是国策,武穆王就不能拒绝。”
一个“国策”,就解决了困挠朝臣的心病,朝臣们顿时高兴起来——
“虞阁老此乃高见……”
“果然,姜还是老得辣啊……”
“虞阁老此计甚高……”
“……”
虞阁老一副老神在在的表情:“武穆王是藩王,不好插手官府的事,但大批流民迁往北境,官府也不好管束,还需要武穆王出面威慑,也不能让武穆王借着藩王的身份撒手不管,届时出了问题,谁也兜不住。”
齐大人眼皮重重一跳,这是要让武穆王插手官府的事?
朝臣们也是一愣,忍不住仔细思量这话。
虞阁老将朝臣们的表情看在眼里,因为查阅过高祖皇帝颁下的国策一应内容,便是谈了这等敏感的话,也是气不喘,心不慌。
“既是国策,当人人奉行,武穆王也不能置身事外,当年高祖皇帝主张迁移流民,就是在辽东都司的协助之下。”
立马就有内侍出了大殿。
不一会儿,就抱了一摞书过来,都是有关高祖皇帝颁发的国策内容。
朝臣们立刻开始翻阅查看。
虞阁老端起茶杯来,靠在椅子上喝茶。
大约一刻钟,便有朝臣道:“虞阁老说得对,既是国策,当人人奉行,北境是在武穆王辖下,边境常有外敌滋扰,攘内才能安外,安置流民虽然是官府之责,武穆王也是当仁不让,须知非常时期,要非常之行事,不可等闲视之。”
让武穆王插手流民安置一事有些不妥。
但是比起流民暴乱频发带来的隐患,这个结果似乎,也更容易被人接受。
况且,还有高祖皇帝前车之鉴,倒也还算顺理成章。
这样一想,朝臣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虞阁老又道:“流民初入北境,也少不了北境士绅们的接纳和赈济,要下一道命令,让他们全力支持官府及武穆王有关流民的安置事宜,违令者,当处以严惩。”
当即就有不少朝臣跟着一起附合:“还是虞阁老考虑得周全,既是国策,当北境人人奉行,士绅们也不能例外。”
武官不能干政,除了涉及战事,这时镇国侯开了口:“狄人也遭了旱,去年秋冬北境已经陆续暴发了十几场小规模战役,想来开春之后,狄人也不会消停,还会继续频繁地滋扰北境,武穆王要主北境战事,还要兼顾流民安置一事,不能因小失大,士绅们必须配合,违令者,当以乱政诛杀。”
此言一出,朝臣们瞬间意识到了严重性。
只有边境安稳,才有他们的太平日子。
就这一件事上,朝臣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北境的士绅们,大多在朝中拥有不小的人脉,但流民也确实是他们的心头大患,既然能将烫手山芋丢出去,甭管丢到谁手里去了,至少自己是安稳了。
当务之急,还是先将流民解决了再说。
至于其他,以后再说也不迟。
几百万流民的去处,不用朝廷出银出粮,就有了着落,既解决了一桩心头大患,也没让他们为难,向来正事拖拉,谋私积极的朝臣们,罕见地展现了雷厉风行的一面,立马拟了折子,递到了寿延宫。
皇上沉迷丹术,已经许久不理政事。
一连四五个月不上朝,朝臣们觉得奇怪,暗暗打探宫中的消息。
但后宫被太后娘娘和兰妃娘娘一起把持,消息不好打探,可越是打探不到消息,朝臣们就越觉得其中有事,就越不死心,这么七弯八拐了打探一通,终于打听到,皇上因久食丹药,脸上长了火疖,折损了天颜,连宫门也封了。
因为不是光彩的事,太后娘娘勒令宫人不许外传。
朝臣们觉得荒唐。
可荒唐之下,又觉得这也理所当然。
皇上是天子,君权神授,何等威严,天颜有损,何以承天启地,又何至于久不上朝,连消息也要捂得死死得。
科举考试都不选取面容有损,身体有残之人,以免折损了朝纲体面。
更何是一国之君呢?
也只有这个理由,能够解释近来宫中动静。
因此,朝臣们也如太后娘娘一般,对此事秘而不宣,朝中之事都是经朝臣商议之后,内阁裁夺,由太后娘娘决断。
太后娘娘看了内阁的折子,盯着“国策”二字瞧了良久:“殷怀玺的腿好了,就如龙游于海,上天入地,覆雨翻云,”蘸了朱砂的笔,悬在折子之上,久久也没能落下,上等的龙泉朱砂墨,湿而不凝,久置而不干,她轻轻一叹,神情变得十分复杂,终于落笔朱批:“罢了,将来总归是要仰仗于他。”
朱公公垂首躬身一旁,双手捧着鎏金的九龙戏珠金盘,上面摆了印泥,以及传国玉玺,笔搁等一应御用之物。
太后娘娘将朱笔,摆到金盘上的笔搁上,拿过了玉玺,轻轻盖上玺印:“拿给何公公吧!”
朱公公连忙躬身退安。
太后娘娘精神不济地靠大迎枕上,看着香案上的博山炉里烟香袅袅,吞云吐雾,眼睛就有些模糊,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殷厉王的生母惠妃。
第602章 拨乱反正
先帝很重农桑,登基第二年,就向全国下了耕耤礼的诏书:“夫农,天下之大命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公卿及以下官员随往。”
皇上在田里亲耕,旁边有众多百姓围观。
周厉王的母妃惠妃,就是耕耤礼时,先帝从民间带回宫里的女子。
惠妃进宫之后,在自己的宫里开了几亩地,春耕、夏酝、秋收、冬藏,活得就像一个普通的农家女。
先帝心疼惠妃。
惠妃直言道:“陛下贵为天子,尚且扶犁亲耕,躬耕以劝百姓,言夫农,天下之大命也,臣妾本就是一介农女,连大字也不识多个,琴棋书画,歌词诗赋更是一窍不通,也只会伺弄庄稼,种些青菜果物,以尊陛下重农固本,彰显陛下仁治大德。”
可先帝却极吃这一套,对惠妃宠爱有加:“春耕、夏酝、秋收、冬藏,四者不失,五谷不绝,爱妃有功。”
殷氏男儿大多都有儿女情长的毛病,身为中宫皇后,她自然懂得利弊权衡。
皇上宠爱的不是权臣之女,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农女,威胁不到她的地位,她也是乐于见成。
因此,她与惠妃关系不错,也为惠妃挡了不少明枪暗箭。
惠妃为先帝育了一子,先帝大为喜欢,取了一个“厉”字。
旁人觉得此字不详,可她和先帝是结发夫妻,如何不知道,皇上唯独对这个儿子,才是真正寄予厚望。
“厉”字,可以通“励”,有励精图治之意。
也可通“砺”,有磨砺,缀甲砺兵之意。
更可通“疠”,有荒、暴、恶之意。
爱之深,才为之计深远,先帝对儿子寄予厚望,却又担心为儿子招来祸端,将一片深沉爱意,诸多掩饰。
殷厉行果真不负先帝所望,天资很是聪颖。
她召见了惠妃:“行儿五岁了,詹事府为行儿启蒙的先生说,行儿天资聪颖,颇具慧根,向皇上谏言,当酌请名师,精心教导,近来皇上一直为此事徘徊苦恼。”
惠妃也不傻,一个五岁的皇子,朝中能教养他的名师多了去,能让皇上徘徊不定的,只有更深一层的东西。
惠妃当即“扑通”跪地:“臣妾一介农女,进宫之后,是得了皇后娘娘庇佑,方能陪伴皇上左右,顺利诞下皇子,为天家开枝散叶,臣妾虽大字不识多个,却也知道,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自当铭记皇后娘娘对臣妾的恩德,旁的不敢奢求。”
她年轻时,被宫里的妃子暗害流产,伤了身子,多年不曾孕子。
她和惠妃关系不错,殷厉行与她也亲近,原是明白了皇上的心思,就有心将殷厉行过继到自己名下。
有了皇上的偏爱,嫡出的名份,以及皇后的支持,皇太子之位非他莫属。
将来殷厉行继承皇位,尊她为皇太后,惠妃为皇太妃。
但惠妃不愿意,便作罢了。
不过经此一事,她是不可能让任殷厉行坐上那个位置。
后来,皇上打消了为殷厉行别择名师的心思。
惠妃因病去世后,先帝悲痛不已,渐渐荒于朝政,因乏人管束,疏于教管,殷厉行也渐渐荒唐了性情。
她借机延揽大权。
挑中了身为四皇子的当今皇上,并且力排众议,在先帝去世之后,扶持他登上大宝,如愿以偿地做了皇太后。
也因此惹了不少非议。
朝臣们私底下觉得,当今皇上的皇位来路不正。
也确实不正。
先帝最属意的皇位人选,从来就不是当今皇上。
先帝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也只有殷厉行。
只是先帝重文轻武,打压武将宗室,致宗室和武官对先帝积怨尤深,她一早与宗室达成了协议,四皇子登基之后,会追复宗室爵位。
有了宗室的支持,先帝也清楚,便是他留下遗诏,殷厉行没有母家支持,也不可能顺利登基。
是她答应了先帝保殷厉行一命,皇上这才松口,立了四皇子为皇太子的诏书。
这一晃眼睛,先帝也去世许多年了,每当夜深人静,她总忍不住去想——
大周朝的皇帝,都有嗜杀的毛病,十个皇帝九个好战,而剩下一个不好战的异类,就是先帝了。
常年征战,以致于国库不丰,先帝自登基起,就打压武将和宗室,重农固本,以休养生息,开启了成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这么一个文治仁德的帝王,真的是她能够威胁得了的吗?
先帝不会轻易就相信她,临终之前许是还留了后手?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她的猜测,可纵观这两年朝中的局势,她竟然有一种“终于来了”的感觉。
太后娘娘轻捻着佛珠,轻叹一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父不父,子不子,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拨乱世,反诸正,那就是王者之道。”
说完,她轻轻阖上眼睛。
沈姑姑轻手轻脚上前,抖着手指,轻探了一下太后娘娘的鼻息,猛然松了一口气。
……
京兆早就关了城门,不允流民进入,但仍然有大量流民涌入京兆,聚集在城外,饱受着饥饿,寒冷的折磨,任由绝望将他们一点一点地吞噬。
“给我,把孩子给我……”城外突然响起了男人的怒吼声。
“不,不行,这是我们的孩子,你不能,不能……”衣衫褴褛的女子,死死地抱着孩子,被她抱在怀里的女孩骨瘦如柴,脏乱的脸上,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懵懂。
四周的人木然地望着他们,有些人则盯着小女孩,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