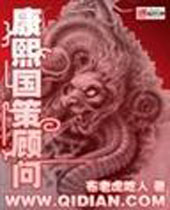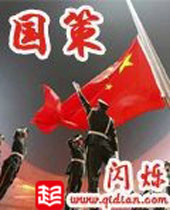新三国策-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与高岱之间,按辈份来讲,他是我的族叔,而真正论及血缘,却要隔了好几辈,小时模糊的听我母亲讲起,我父亲与高岱算是堂兄弟关系,父亲早亡,打我小时我们便寄住在高岱家中,一直到高家被官府抄没。
高岱对于我来说,虽然是他使得我的童年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但若不是他,我在幼年时也不可能受到良好的启蒙,我们母子的生活一开始就会象我这十余年过的一样,每天为了一口饱饭而苦苦挣扎。
即便在我以后,成了大户人家的家奴,也因为能够识文断字,而被主人家差遣来服侍公子陪读,这使我才有了今天这般的学识。
望着岱叔渐已斑白的两鬓,我感慨万分,就实际的年纪,岱叔才不过三十出头,但现在看起来,他却已象是四十左右的人,这十余年来,颠沛流离的日子留给他的除了苦涩,还是苦涩。
……
第二天,我在豫章大宴众将,一则庆贺我军兵不血刃收降山越诸部,二来是为刘晔、顾雍诸人接风洗尘。
席间酒过三巡,华歆已微有醉态,长身而起,说道:“豫章地辟,今能迎驾诸位江淮名士,实乃晔之幸也,歆年少时曾听人言,欲起兵成事者,必先取幽、燕,联结秦、雍,固青、徐、豫、冀为腹地,延揽英雄,乘时而动,驱胡虏于北地,下江南而取吴楚,如此天下可得矣,诸君以为如何?”
华歆乃是平原高唐人,高唐齐名都也,衣冠无不游行市里,华晔自识才高,见众多吴中名士到来,心中隐有些不服,故出言相难。
我不动声色的抬眼看去,却见顾雍脸色平静,而朱桓却奋然而起,道:“太守之言是讥江南无豪杰乎,难道不知昔日项王举三千子弟灭强秦之典故?”
华歆一阵大笑,道:“项羽再勇,也不过垓下一匹夫耳!”
此言一出,诸人俱怒。我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华歆是中原人氏,他出言贬低项羽,也是正常,毕竟在楚汉相争的得胜了的正是开创三百余年汉室的高祖刘邦。
但现在,他这一说却是惹恼了在座的大多数人。
我见顾雍脸上也隐有怒容,朱桓更是要拍案而已,知道自已再不制止,事情将无可收拾。
想到此处,我遂倏然站起,举杯大声道:“有道是乱世男儿,须以身当剑,中原纵有虎狼,岂能阻我前行?方今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我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我凄怆伤怀。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我百年之后何恨哉!”
这一番话我是有感而发,全属肺腑之言,说得端是慷慨激昂,直抒心中之意,倒也痛快淋漓之至,顾雍、朱桓诸人闻我之言,脸上俱是动容。
顾雍沉声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自遭黄巾离乱以来,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少冲当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如此方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
顾雍之言与我屯田养民,固土扩张的举措不谋而合,我在豫章屯田伊始,太史慈、华歆等皆以为当先强兵以退孙策,皆不赞同,此时我听得顾雍之见,顿感顾雍之远识,作为蔡邕的亲传弟子,顾雍的才能比之华歆来,也许更适合做一郡之守。
我大喜道:“来,顾公,子扬、子鱼,诸位请畅饮之!”
当日,我力排众议,以顾雍为功曹,分管内政事务,功曹虽然比太守要差了一级,但在郡吏中地位最高,有顾雍辅佐,豫章的内务我也可以少操些心,同时我令朱桓为裨将军,协同太史慈镇守石印山防线,孙策虽然答应了谋和,但他在丹扬仍驻有陈武的精锐宿卫二千余人,在曲阿还有周瑜领军镇守着,我切不可掉意轻心。
“少冲,让元叹分管内政,恐有不妥!”宴后,刘晔追随我到府中,谏道。
我道:“以顾公之才德,区区功曹并不为过。”
刘晔近前一步,道:“元叹有佐国之才,功曹之职只是小了,但少冲可知,内政事务向是子鱼在掌管,如今要分了大部给元叹,子鱼恐有不悦。”
刘晔说的这一层,我想是也想到过,方才我与华歆商讨任命时,也察觉到他脸上闪过的那一丝不快,但以顾雍之才干,若是因为这个而不去利用,实是可惜。
刘晔想是知道我的想法,又道:“以晔之见,南方的庐陵虽定,但各部对我军仍存有异心,若他日有风吹草动,必生变故,莫如效仿汉武帝太学方略,在豫章筹建一所学堂,一部分学员从百越各部落宗帅首领子弟中挑选,一部分从屯民和流民中招募,如此假以时日,可为豫章培养无数可用之材。”
我道:“子扬之言甚好,只是何人可堪这祭酒主管之职?”
刘晔笑了笑,道:“元叹岂不是最适合的人选。”
我闻言大喜道:“子扬深谋远虑,我依言而行便是!”
豫章城南,苍松翠柏之间,巍巍莫厘峰下,掩映着一排整齐的竹舍。
房舍虽然简陋,但却占地百亩,气魄宏大。
这里是正在筹建中的豫章新学府――天威学府地址。
经过二个多月的精心准备,第一批五百名十四五岁的新生已经全部报到,其中近一半学生是从世家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四分之一是山越诸部宗帅的子侄辈,剩下的四分之一从普通百姓和南渡流民中召收的庶民子弟。
天威一词,意思便是天朝威仪不可侵犯,可惜,自黄巾乱起以来,汉室的威严早就被一次次的战火所践踏,如今的皇帝更是被割据的强豪挟来挟去,已然成为了被利用来讨伐敌对势力的工具。
早在汉武元朔元年,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便下了一道“兴廉举孝”的诏书,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把它制度化,哪级官吏“不举孝、不察廉”就免职罢官。但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和宦官外戚的夺权,各级官僚豪强为扩张自已的势力,极力推行愚民政策,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至汉末时以“德行”和出身门第晋官举廉仍是主流,能接受文化教育的,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般庶民百姓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
这种情况,就是在光武中兴之时也不过是稍有所改善,待到了灵帝即位时,用人首先是看重资历,担任一定的官职还要有相应的财产标准,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凡是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都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这种看似公平的推举孝廉的体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人才的退化,并影响到了人才的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巾之乱之所以能拥有摧毁汉王朝的力量,与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不甘没落无名的庶民支持是分不开的,参加黄巾起义的人员中除了最底层的佃农、奴仆外,还有出身贫寒的文人志士。
既然朝廷黑暗,没有了向上的途径,唯一的选择也只有反抗。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即便是从军行伍,我也立下过战功,但却因为家奴的身份,受到张英等人的歧视,在刘繇处也长久得不到重用。
如今,我虽然占了豫章,但兵微将寡,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一两员将、七八个人,如果我仅仅满足于从世族子弟中录用人才,最后的结果难免是人才凋零,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
若要成就大事,当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我早有心筹建一所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只是碍于战事吃紧,脱不出身,手下有限的几个将领如太史慈、华歆、刘晔、甘宁又都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所以才迟迟未能有所动作。
现在顾雍等人的到来,使我如虎添冀,底气也慢慢足了起来。
而且豫章眼下暂无战事,我正好可以静下心来抓一下后备人才的培养。
学府将分为十个班,每班五十人,一年级主要是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如《诗经》、《论语》、《孙子兵法》等;二年级将根据学生的各课成绩,分成文、武两科,文科主修商业、法令、典农等内政事务,武科主修武艺、谋略、行军、布阵、军演等战事;三年级则是对学生文武能力进行综合评定,测试其融会汇通的程度,并在实习中选拔优秀人才。
第一批新生中,出身世族的占了一半多,这主要考虑到世家子弟接受过基础的文化教育,起点比贫寒人家的高,而且我现在还需要豪族宗帅的支持;另外,让山越诸部选拔子弟参加军校,既可以从异族中发现人才,又可加深我与越族后代的感情。
而留给庶民的名额虽然不多,但我想对于因出身卑微,苦无建功立业机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第一批的五百个少年,虽然一时尚不能派上用场,不过若倾力培养,那么不消几年,就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他们正处在树立志向的时刻。
在今后的三年里,陪伴他们的将是荣誉、忠诚和信念。
他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证明自已是最优秀的。
第二十九章 长沙来使
我站在天威学府的操场之上,五百双炽热而年轻的眼睛看着我,等待着我一声令下。
顾雍站在我边上,轻声感叹道:“论世家万物,自古栽花木易活,育人才艰难,这个师友祭酒的位置看来不好坐啊!”
正祭酒义不容辞是由我担当的,顾雍在我和刘晔的劝谏下,爽快的答应做了具体管理学府事务的师友祭酒,与他一同到学府的,还有许邵等好几个豫章的名士。
我笑答道:“顾公可知,能用众力者,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者,则无畏于圣人矣!”
顾雍闻言,肃然道:“少冲兄此言,真是一语道破玄机啊!”
我笑道:“适才我听顾公的话,似有知难而退的意思,这可不行啊!豫章未来的希望现在都你手里握着呐!”
陆逊站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他身后是陆绩,还有顾雍的长子顾邵等人,他们都是我亲自点名的学员,以陆逊的资质和在由拳之战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经过学府系统的培训,相信不悄多日,必能成为统兵一方的帅才。
“扬我天威,永镇我邦!” 这是我给学府成立时撰写的八个字。陆逊第一个领头,大声喊道。
随后五百个稍显稚嫩的声音整齐划一,喊声高昴直冲云霄,透着少年特有的热情和火焰,少年童稚的声音犹在山谷中回荡,余音不绝。
如此热血健儿,假使我麾下有上万骑,何愁大事不成?
“扬我天威,永镇我邦!” 我也在心里默默的念着,这是我心中不变的理想。
回到城中,已是天色渐晚,我正欲歇息,负责接洽的许靖来报,说是长沙太守张羡派使者求见。
我听此消息,想道:“长沙与豫章分属荆扬两州,不知张羡此时派使者前来是何用意,张羡久有图谋自立之心,莫非是为此而来?”
我心中如此思量,嘴上道:“召!”
稍歇,只见许靖领了一面容方正的中年文士来,那人见我年纪如此之轻,显然有些意料不到,怔了一下,随即施礼道:“长沙桓阶见过豫章太守大人!”
我道:“无须多礼,临湘桓伯绪之大名早有耳闻,今日不知桓先生远道而来,有何公干?”
桓阶道:“阶此来,乃为解将军之忧而来!”
桓阶这一答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解我之忧,不知桓阶的葫芦里会卖出什么药来,我倒要看看,想到此处,我道:“豫章宗贼俱平,民殷府丰,有识之士莫不相投,此乃盛世之象,试问先生,忧从何来?
桓阶不慌不忙,踏上一步,近前道:“阶斗胆问将军,豫章比之荆、扬两州孰大?”
我道:“荆州治下八郡,杨州也有六郡,豫章不过为扬州之一郡,自然不能与之相比。”
桓阶又道:“既如此,阶再问,将军比之刘表、孙策,孰强孰弱?”
桓阶这连续的发问无礼之至,我斥喝道:“自是彼强我弱,此三岁小儿皆知耳,先生如此相问,莫是要休辱我吗?”
桓阶道:“将军息怒,若单以豫章一地之力相抗刘表、孙策,确不能也,此为将军之忧,阶私下为将军计,若要抗衡强敌,当效仿苏秦合纵六国,共御强秦之策,联合近邻,互为倚重,此存亡之道也。”
桓阶的意思我终于明白了几分,他要我联合近邻,豫章左近,相邻者除刘表、孙策、袁术外,只有荆南四郡了,看来桓阶的意思是要说我与张羡结盟了。
我假作不知,倾身问道:“豫章之邻,莫不是虎狼之辈,何有倚重可结交之力?”
桓阶见我有心动之色,心中暗喜,道:“长沙太守张羡刚直敢言,以礼义深孚民望,可当为将军之友也。”
我道:“愿闻其详!”
桓阶此时一摆衣袖,道:“阶此来,实受长沙太守张羡大人之托,特来贵郡商谈结盟之事?”
我心里一动,莫不是张羡欲脱离刘表自立,这才使桓阶来向我结盟,豫章紧邻长沙、桂阳,张羡若要自立,当先保后方稳定,因此我的态度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这么说来,刘表还没有完全控制荆州全境,起码荆南四郡中最大的长沙郡太守张羡与他不睦,对于我来说,这倒是一个突破的机会。
我道:“先生请入内详谈!”
从桓阶口中,我获悉了荆州各派势力争斗的内情。早在初平元年,刘表初到荆州,江南宗贼大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刘表单马入宜城,与荆襄豪族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谋划,乃使越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众,随后刘表檄文过处,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平定了荆襄。
不过,这种以权谋而非战力取得的成果注定是不安稳的,在荆州安宁和平的表象后,正蕴藏着激流涌动。
随着刘表在荆州地位的稳固,施政之初联合的同盟势力开始分化,剪除不合自已胃口的异已分子对于刘表来说是顺里成章之举,而长沙太守张羡则是首当其冲的人选。
长沙郡,在荆南四郡中最为重要,它北有洞庭重湖,浩淼无涯,阻隔关山,是长沙的北部门户,南有五岭屏障,山势逶迤,形势险峻。更有发源于岭南的湘江流贯全境,连通南北,交会东西,素为南部疆域的重镇名城。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不安排自已亲信之人怎行?而张羡与刘表素来不睦,被清除也是当然之事。
看到桓阶把话都挑明了,我也不再虚与委蛇,单刀直入,问道:“长沙与豫章分属荆扬两州,张使君此番欲与我结盟,莫非有自立之意?”
桓阶听我一语道破其来意,沉声说道:“刘表刻薄寡恩,亲小人远君子,我家主公素来刚直,言语间不睦之处甚多,故刘表早存废我主之心,只一直不得便耳,今荆州大局已定,刘表已属意使蒯越代领长沙太守,我主不从,故不得已欲反之。”
果不其然,张羡此番差桓阶前来,实是为探听我军虚实而来,如果我同意结盟,则张羡自立之心将更加坚定,因为以长沙、豫章之力,山河之险,虽不足以击败刘表,但至少自保不成问题。
我道:“刘表坐拥荆襄八郡,手下文有蒯良蒯越,武有文聘蔡瑁,精兵强将不下十万众,张使君以区区长沙一郡与之抗衡,此如乳兔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