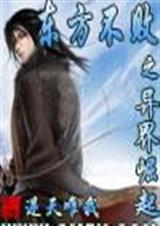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圆满,但也堪慰平生了。
9月25日,胡适写信给韦莲司:“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固我心。那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到的景色多么优美,多么带有象征意味啊!那象征成长和圆满的新月,正在天际云端散发出耀人的清辉,美化了周围。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灭,新月终成满月。”
和韦莲司的灵肉之交,使胡适对美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胡适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就是当年的小伴娘曹佩声。1921年5月初,胡适接到三嫂的妹妹曹佩声的杭州来信,请他为《安徽旅杭学会报》作序。胡适想起当年自己婚礼上这位15岁的小伴娘来,慨然答应,从此与曹佩声书信往来。
曹佩声,乳名行娟,学名诚英,1902年生于绩溪旺川村,其同父异母姐姐是胡适的三嫂。曹佩声的母亲是曹佩声的父亲经商到四川时买下的小妾。曹佩声父亲早逝,17岁时便由母亲做主嫁给了同乡胡冠英,后在留美的哥哥曹诚克鼓励下,入杭州浙江女子师范读书。
1922年底,曹佩声因与胡冠英性情不合,解除了夫妻关系。胡适得知后,便于1923年春到杭州游玩,顺便探视寡居的曹佩声。胡适一抵杭,曹佩声便张罗同乡来看望胡适,并陪胡适游山玩水。这次杭州之行虽然只有四天,但在双方感情的湖水中却投下一颗分量颇重的石子,在彼此心中泛起层层涟漪。曹佩声“縻哥縻哥”的亲切声音时常在胡适耳畔回响,她那美丽而略带些忧郁的神态令他心痛。临别前,胡适写了一题为《西湖》的诗:“十六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而使我病得更厉害了!然而西湖毕竟可爱,轻雾笼着,月光照着,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诗中的“伊”明写西湖,暗写曹佩声,其中“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系指曹佩声因不生孩子遭夫家歧视,以及她离婚一事进入非议,一语双关,意味深长。
曹佩声自然读懂了胡适的心声,当然也从他眼神中发现那份关爱之情,多少次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胡冠英能像这位“縻哥”一样有出息,没想到自己和胡冠英离婚不久,这份梦寐以求的爱竟突如其来地降临在自己身上。她的心为胡适怦然而动。
6月初,胡适收到曹佩声两封情意绵绵的来信,忍不住重返杭州,与心上人相会。这次来杭,胡适和蔡元培、高梦旦同行,他们先是住在西湖边上的新新旅社。6月24日,蔡元培、高梦旦离开杭州后,胡适干脆搬到烟霞洞一家临时旅馆住下。此时,曹佩声所在的学校也放了暑假,曹佩声便上山与胡适同居。胡适把这段岁月称之为“神仙生活”。
胡适在曹佩声的陪同下,经常到陟屹亭散步,看桂花,下棋,讲莫泊桑的小说。9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记道:“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佩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下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个莫泊桑的故事。到4点半钟,我们仍循原路回来。”9月14日,“同佩声到山上陟屹亭内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16日,“与佩声下山。她去看松竹友梅馆曹健之,我买了些需用的文具,到西园去等她。……后来佩声回来,说没见着健之。我们决定住清华第二旅馆,约健之晚上来谈。晚上无事,我打电话邀柏亟谈了好一会儿。健之他们也来了,谈到夜深才去。”曹健之是曹佩声的亲属,也是胡适三哥的外戚。由此可见,胡适和曹佩声的关系基本上已到了半公开的程度。
1923年,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曹佩声随侍在侧。9月28日,新月诗人徐志摩应邀到烟霞洞赏月,尔后徐志摩又邀胡适到家乡海宁观潮。胡适带曹佩声前往。胡适日记中记道:“今天为农历八月十八,潮水最盛。我和娟约了知行同去斜桥,赴志摩观潮之约。车到斜桥,我们先上了志摩定好的船,上海专车到时,志摩同精卫、君武、叔永、莎菲、经农和瓦沙大学史学教授埃勒里一齐来,我们在船上大谈。”胡适海宁之行,他与佩声的关系初露端倪。徐志摩在《西湖记》中写道:“到斜桥时适之和他表妹等已在船上……我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
第二部分白话文倡导者 胡适(12)
10月初,曹佩声要回学校上课。胡适也要回上海做事。胡适在枕上记下了分手前夜的情思:“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惨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目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0月4日,胡适记道:“娟今天回女师。”又记道,“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胡适回到北京,便提出要和江冬秀离婚,江冬秀以母子的死相威胁,胡适到北京西山躲避。在西山,胡适认真回顾了一年来的感情轨迹,在日记中记道:“这一年可算是在病中过了的。……七个月的光阴都是在南方养病,这一年没有在北京大学上课,也没有做什么重要的著述。其中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作的诗颇较前几年多,即取名《山月》。”并随手写下一首小诗:“放也放不下,忘也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笑。”这时,徐志摩来信问胡适和曹佩声进展如何?胡适以诗答曰:“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胡适性格含蓄懦弱,身处逆境常常求助于思想上的解脱,而很少行动上的悖逆,偶有反抗也难得持久。和曹佩声的爱情固然浪漫,但那毕竟是神仙境界,在江冬秀的压力下,也只得向传统妥协,长叹一声:“我决计‘下山’来了。”曹佩声因胡适离婚不成,只好到医院堕胎,这次打击使她受到了强烈刺激。
为了安慰曹佩声,胡适和她暗中联系,他们的通信,多由胡适的侄儿胡思猷传递,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则为胡、曹相会提供场所。江冬秀知道后,迁怒于胡思猷和汪孟邹。据胡思猷夫人李庆萱《回忆四叔胡适》中说:“思猷姨娘曹佩声与胡适恋爱书信往来,怕被遗失,留人话柄,所以都交由思猷经手传送。江冬秀知道此事后,迁怒于思猷。到了思猷有求于他们的时候,必然遭到江冬秀报复。”40年代,亚东图书馆最不景气时,江冬秀偏雪上加霜,去讨胡适的版税,令汪孟邹叫苦不迭。
因为不能长相见,胡适甚至提出,让曹佩声另找生活中的伴侣,但曹佩声却无法释怀,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想投考胡适任教的北京大学,但怕扰乱胡适平静的生活而放弃。当年秋天,曹佩声由胡适介绍,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农艺系学习,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有一段时间,为使曹佩声专心学业,胡适中断了他们的相见,但曹佩声常用书信或诗向胡适表达自己的心声,胡适劝她:“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忘却好,莫教迷疑残梦,误了君年少。”后来,胡适激情难遏,便借南行之机,常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与曹佩声约会,并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
曹佩声留校任教后,她的毕业论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一家农业杂志上。胡适看到她有所作为,便联合中央大学,推荐并保送她于1934年秋到美国人自己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37年,曹佩声获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归国后到安徽大学任教,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而此时的胡适,却阴差阳错地赴美任驻美大使,眼见八年的等待又成泡影,曹佩声失望之余,给胡适写了一首诗:“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未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娥眉神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思情牵系。”信无邮址,仅有邮戳上“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原来,花容月貌的曹佩声一向侠骨柔肠,和胡适迎面错过使她痛苦万分,绝望之余,竟欲遁入空门,上峨眉山出家,后被其兄曹诚克力劝下山,但却因此害了一场大病。
1943年春,身体渐渐康复的曹佩声到已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并于是年秋托大学同学朱汝华带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一首诗:“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病情在。年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
抗战胜利后,曹佩声随复旦大学迁往上海,此时的胡适已是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底,胡适从北京乘飞机经南京飞抵上海,当时曹佩声婉言相劝胡适说:“縻哥,你留下吧,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下去了。”可惜胡适没有入耳,终于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从此两人竟成永诀。
曹佩声一直未嫁,1952年9月17日离开上海赴沈阳农学院任教,1968年退休后借居在杭州汪静之、符绿漪夫妇处,并将一生所写的日记、诗文以及胡适给她的信交给汪静之保存,不幸毁于文革。1969年,曹佩声回到绩溪老家,在绩溪县城租了一间民房暂住。在绝望和病魔摧残下,曹佩声于1972年1月18日病逝于上海。
第三部分现代作家 瞿秋白(1)
瞿秋白(1899~1935年),江苏常州人,现代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
1923年,24岁的瞿秋白,和陈独秀一起自莫斯科回到北京,开始独立地踏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爱情女神来叩这个年轻人心灵的大门了。
由于柯庆施和施存统的介绍,秋白在南京认识了王剑虹和冰之(丁玲)。这是两个来自湖南的叛逆女性。
王剑虹,1902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后迁居湖南。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思想进步,口才流利,是一位有思想见地,才华出众的女青年。
1922年初春,冰之等人就是在她的宣传鼓动下,和她一起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从结伴离开湖南起,剑虹和冰之结为挚友,她们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床而眠。在平民女校读了半年,又感到不满足了,决定去南京自己学习,遨游世界。没有想到,在南京她和秋白相遇了,在秋白的劝说和吸引下,她和冰之决定重回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像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上海大学设在偏僻的青云路上,是些破旧的里弄房子,设备虽然简陋,但在这里曾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邵力子任校长,实际上却是由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人负责的。秋白当时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他白天讲课,而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到剑虹和冰之住的小屋去,给她们讲文学,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不但讲文学,而且讲社会生活。特别是后来,为了帮助她们两人领会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就教她们直接读原文的普希金的诗,边读诗边学俄语。
1923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瞿秋白又来辅导王剑虹和丁玲学俄文了。
剑虹和丁玲正在边查字典边阅读报刊。瞿秋白静静地观察,王剑虹那黝黑闪亮的发丝,燕尾如翅的娥眉,高低适衬的鼻梁,似乎比丁玲更漂亮一些……当瞿秋白正看得出神时,猛不防,王剑虹一抬头,突然发现瞿秋白正痴呆地注视着她。王剑虹心里隐隐跳了一下,面容立即为之变红,便迅速埋下头去看书本。瞿秋白也反应过来了,心中一惊,不好意思地收回了目光。
就在这种频繁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隐蔽而又神秘的感情悄悄袭上了秋白的心头。他为此感到苦恼,平日谈论问题常是滔滔不绝,现在却沉默不语了;他也不再去剑虹和冰之的小屋了。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要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感到意外和不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要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出来,成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
丁玲来到离学校不远的瞿秋白家,这是一排西式的楼房,瞿秋白正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瞿的弟弟云白把丁玲引到楼上瞿秋白住的房间。丁玲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
“他
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
谁不钦羡、敬重?
但,
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自尽的事。“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第三部分现代作家 瞿秋白(2)
瞿秋白握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宿舍去了。当丁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乱着他们写的字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