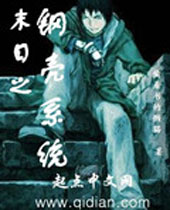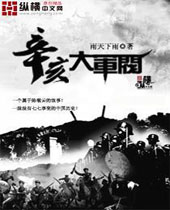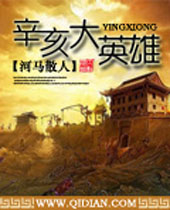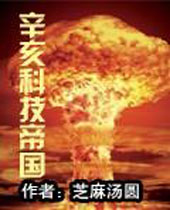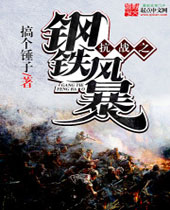辛亥之钢铁基地-第1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人,不但天津机器制造局、纺织局、太原机器制造局等洋务工厂无法开工,就连轮船招商局都陷入停顿,每天都要亏本一大笔钱,另外电报局、矿山、铁路等的建设也全部停止,各大银行一堆坏账烂帐,就连洋行也是如此。橡胶股票卷走了大部分财富,没钱开工资就保不住工人,没钱就无法维修设备,没钱就无法修铁路。甚至天津北洋大学也因为资金断裂而停课,听说许多学生都跑到南边去了!”蔡邵基诉苦道,其实这些东西他早就说过,不但那些学生,不是连詹天佑都跑了吗,铁路停工,还被官场排挤,詹天佑赋闲在家,放在自己身上也早跑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二章 意料之外
袁世凯摆摆手,示意不要再说了,他就不应该提起这个话题。股票的事自己也损失惨重,整个北洋军没了军费,要不是英国人硬着头皮再次提供贷款,北洋早已崩溃,绝不是现在的样子。即使如此,袁世凯也是苦苦支撑罢了,他在等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吕梁开启南北和谈,这样一来不但能保全北洋,还可以将烂摊子抛给吕梁。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让崧生办好此事,最好能借容闳直接见到吕梁,通过容闳表达我们的意思也算是第二个选择。总之,我们不能再等了。”袁世凯说出此话后,屋内一阵沉默,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北方烂成什么样子,朝廷从上到下,从王爷到县令,都在拼命捞钱,试图挽回股票的损失。民间用民不聊生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至于河南旱灾,这件事根本没有摆上议程。
“大人,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干等着吕梁发出信号,也得主动做些什么,好让吕梁明白!”杨度贼兮兮的说道。
“哦,咱们不是派出梁敦彦活动嘛,难道让我公开说明愿意和谈?那与投降何异,到真正谈判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争取利益?”
“非也,大人,我指的是朝廷。太后去世后朝廷一盘散沙,那些满人只不过是等死罢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推他一把,干脆让他退出去呢?”杨度语出惊人,这种想法在每个人的闹好中都浮现过,但立刻又被“大逆不道”之类的词赶走,文人最重视气节,即使属于北洋集团,口头上也会说忠于朝廷。
没想到最后这句话竟然被所谓的“国学大师”杨度说出来,不能不让人惊讶。在暂时的沉默后,有人发现了袁世凯微妙的表情,顿时反应过来,这个杨度才是聪明人!他根本就是替袁世凯说出这话!
于是第二个幕僚开口了:“皙子所言极是。我们一旦迫使清廷退位,那么北方就有大人完全做主,再也没有其他人在背后指手画脚。之前南方顾忌的,无非是与我们和谈后朝廷的态度罢了。如此看来,此举大大有利于国家之和平,乃是惠利万民的举动,请大人一定要同意啊!”
此后屋内立刻热闹起来,有人从战略全局的角度分析。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更多的老学究则咬文嚼字、摇头晃脑、引经据典,综合起来就会发现,清廷不退位就是罪大恶极,甚至有人用“从龙”这个词来试探袁世凯的态度,立即被袁世凯阻止。
当皇帝啊,谁不愿意,袁世凯当然也想,不过也就是想想罢了,自己愿意、手下愿意管个屁用。怎么不问问南方五十万大军愿不愿意?
“老夫乃是国之栋梁,以毅勇侯(曾国藩)、李中堂为榜样,从朝鲜开始,朝廷就待我不薄,尔等这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境地?此事休得再提!”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眼角的笑意谁都看得出来。
“大人忠孝仁义举世无双,我等佩服。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满清早已没有统领天下之能力,为了万民,还请大人深思啊!”说着杨度跪倒在地。就差没说出“皇上”来了。
其余人也随之跪倒,袁世凯笑着一一扶起,说道:“此事事关重大,尔等先盘算一下。等梁敦彦那边的酒会结束,看看南方到底是什么态度后再作打算。”
这就是让手下们开始制定计划,准备满清退位之事了,众人大喜。到时候满清退位,国家不能一日无主,还得有皇帝啊。袁世凯是皇帝,自己等人不就是身边的亲信大臣嘛!至于总统,那玩意是洋人叫的,跟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是皇帝好,咱们华夏几千年来都叫皇帝,传统怎么能轻易改变?
三日后,梁敦彦带着袁世凯殷切嘱托,欣然前往上海自强连锁大酒店。在袁世凯的密电中,稍稍透露出逼迫满清退位之意,此事梁敦彦是同意的,不过一同发来的杨度的密电就让梁敦彦无法赞同,杨度的意思虽然隐晦,但也能明白,那就是满清退位后,必须再有一个帝王领导国家。
狗屁!白日做梦的国学大师,整天就做着皇帝梦,现在这个时代是皇帝的时代吗?看看上海满大街的高楼大厦、满地跑的汽车电车、江里游的巨型轮船、郊外数不清的大型工厂,那些人就像是井底之蛙,闭着眼睛不管外边世界的变化,沉醉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坐着皇帝大臣的美梦!
让人悲观的是,似乎自己的主子,袁世凯也有这样的打算,这让梁敦彦觉得自己是明珠暗投,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华国的阶下囚。回想自己从1904年九月和杨度到武汉并于章台炎交谈,无功而返后袁世凯命自己常驻南方,最好与华国上层、甚至直接与吕梁接触,寻求保住北洋集团的方法。但是在这里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这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越觉得这里才是国家的希望所在。
甩开乱七八糟的想法,现在最重要的是参加那个酒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向华国上层传达和谈的方法。自己毕竟跟随袁世凯多年,要不是他,自己可能和许多留美幼童一样失去未来,不要说身居高位,就连吃饭都很艰难。
“崧生,欢迎欢迎,就等你了!”张康仁早已在门口迎接,见到梁敦彦后立即将其引到举行酒会的大厅。
一路寒暄,抵达大厅门口后,两名服务员为其推开大门,里面的景象让梁敦彦有些花眼,恍惚间,他被许多人一把拉住,各种问候的话语萦绕在耳边。
都是当年的留美幼童,满大厅估计七十多人,多年不见,不少人已经满头华发,虽是中年的年纪,仍可看出生存的艰辛。当一名七十多岁的老者走过来后,梁敦彦终于从恍惚中清醒,赶忙上去弯腰问候,正是所有人的先生——容闳。
“先生,身体一向可好?多年不见,崧生甚是想念。”
“过来坐下吧,几十年了,老夫也很想念你们这些娃娃。心想趁着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动,让康仁组织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你们都找来,再让老头子我看上一眼,心里就满足了。哎,说起来还是老夫对不起你们,没能挡住朝廷将你们遣送回国,学业未成不说,还没有妥善安置,耽误了你们的将来,想起这件事来我就感到痛心。”容闳说道,当年的留美幼童在光绪七年的时候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后饱受轻视,像詹天佑这样学习工程的,却被派往广州教英语。
“先生不必自责,崧生一直非常感谢先生。”
从激动中恢复过来,酒会随之开始,自助形式的酒会让梁敦彦可以与大家随意走动交流,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让他想起了在美国的时候,几十年颇受约束的官场生涯,让他忘记了这种感觉,现在看来,感觉很不错!
不过,有一点让他非常别扭,那就是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留辫子,在美国时同学们也是剪去辫子的,不过回国后大部分顺应形势又留了起来。那么他们,都是为华国工作吗?
“怎么样,崧生,感觉还好吧!”张康仁忙活一阵后来到梁敦彦身边问道。
“康仁,这个酒会是你组织的,我问你一句,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留美幼童?他们都为华国服务吗?”
“呵呵,崧生有所不知,当年我们被迫中断学业,抵达上海后被关在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最终的工作安排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庙堂上的争斗使我们成了受害者,后来我在我哥的帮助下再次出国,只是结局也不怎么好。在国内的人你应该清楚,像你、詹天佑、唐绍仪、蔡邵基等人学有所用、身居高位之外,大部分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就算是在朝廷铁路部门、矿务部门、交通、外交、军队等部门做事的,也很难一展所长,大部分在官场斗争中跌宕起伏。”
“事情在1901年末发生变化,现任华国总统吕梁先生当时派出一支秘密小组,接触我们这些人,后来北伐后华国建立,许多身在南方的留美幼童随之进入华国系统,并在各自领域开展工作。”(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三章 和谈开启
事情说起来简单,当时却经历了不小的波折,许多留美幼童当时在南方安家,年过半百,在国内环境的洗刷下早已失去为国效命的雄心,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吕梁派出的人先经过一番努力后找到那些人,多次劝说都被拒绝,当时振国党还没有开始北伐,不被看好也属正常。直到北伐胜利、振国党控制整个长江以南后,这些人才不得不转变身份,当然,事实证明华国政府能充分发挥这些人的才能,并使其享有与才能相匹配的待遇。
梁敦彦听完也感慨一番,抿了一口酒掩饰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低声说道:“我可是为袁世凯服务的,算是北洋集团的高官,这么明目张胆的邀请我参加酒会,不怕政府忌讳吗?”
“哈哈哈哈,这一点你还是向容先生求证吧,他现在是研究室主任,可以直达天听,你问他,相当于问华国总统。”张康仁大笑离去,搭桥的任务已经完成,就看梁敦彦毛顺不顺了。
梁敦彦得到暗示立刻屁颠屁颠的跑到容闳面前,刚才第一次见面,不合适往深里说,又因为容闳四周人太多,直到现在梁敦彦才瞅准没人的机会跑过去。
“先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梁敦彦低声说道。
“老头子我说话直你可不要怪罪,在华国工作几年,慢慢的沾染上他们直来直去的行事说话风格,感觉倒也不错。崧生是想问关于华国和北洋之间关系的问题吧!”容闳乐呵呵的说道,年纪很大,精神却很好,有时候还能幽上一默。
“是的,崧生正想问这个问题。先生慧眼如珠。”
“什么呀,你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上海、武汉、广州三地上蹿下跳,谁会看不到?袁世凯也真够着急的,让你这么忙活。说实话,跟吕梁总统比起来,袁世凯的眼界太低。他可知道现如今华国在吕梁的带领下开疆扩土,接连收回台湾、琉球等地,将日本完全击败,一雪甲午之耻。他袁世凯在朝鲜多年,应该最知道击败日本人对于华夏来说是什么样的功绩。”
“要我说袁世凯已经走上了歪路,正事不干,光琢磨着怎么抱洋人的大腿,琢磨着怎么保住自己的权利,他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脱不开旧式官僚的范畴。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迟早要被抛在身后。崧生你不一样,你接受过美国人科学文化的教育,眼界开阔,应该能看清楚,单说一点,袁世凯手里那二十万北洋军是华军的对手吗?要不是对日战争的牵制,华军早就打过去了。那二十多万人不是袁世凯的筹码。吕梁总统顾忌的,只是内战会造成更多的国人死伤罢了。比起来,看看吕梁先生的胸怀!”
容闳唠唠叨叨一大通,教训起来不比当年差,梁敦彦也只能唯唯诺诺的听着,还得点头应是。不过,这些话并不是简单的唠叨。里面的内容说明了很多问题。华国方面不是放任北方不管,而是因为对日战争没有抽出手来,现在战争结束,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北边!而且人家说了,凭借北洋二十多万军队根本挡不住华国的进军。这是威胁,更有可能是一个信号,一个可以和谈的信号,要不然不会说出来,直接打过去好了!
这场酒会果然有内容,梁敦彦大喜,既然容闳喜欢直来直去,拿自己也直说好了:“先生,其实袁世凯也不想看到内战爆发导致民不聊生,他不仅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还得为北洋集团上上下下的前途考虑,所以才派我在这边活动,希望能与这边展开会谈,共商国家之未来。”
“屁!还说为民生考虑,河南大旱,上千万人受灾,几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怎么没见悲天悯人的袁世凯出来救灾?”
“这,先生也知道,北方到处受灾,朝廷又因为股票风波损失惨重,实在是力不从心。”
“那你转告袁世凯,华国这边粮食足够、救助灾民的心情非常迫切,满人和北洋救不了,我们华国愿意出钱出粮救灾。河南的事情解决,才可以谈国家未来这样的大事,至于北洋上上下下和袁世凯的前途,你放心,吕梁总统不是不讲理的人,多少满清的官员都成为华国系统内关键的成员?更别说人才济济的北洋了,只要是人才,吕梁总统都会采用。”
梁敦彦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场酒会的目的是救灾河南?华国主动联系自己的目的是救助灾民?想不到啊,实在想不到!
在这个年代有多少人能想到官方会将救灾放在头等大事的位置上,有谁会想到人家讲低贱的灾民放在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有谁会想到救灾竟然能和会谈这样的大事平起平坐、甚至超出一等?
就算是这些留美幼童都不会想到,在北洋内部听说河南旱灾的都不多,更别说救灾、重视了!不过,容闳还是说明了,华国同意和谈,尽管条件是救灾河南,只要同意和谈就好,这样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估计北洋上上下下也能保全,得赶紧将这条消息传回北京,让袁世凯等人高兴高兴!
一天后,张康仁再次见到梁敦彦,这一回双方算是以官方的身份进行接触,张康仁要求北方让出一条道路,让华国的救灾队伍可以深入河南,从湖北到河南开辟一条灾民迁移之路。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中转点设置在哪里,太过深入河南,恐怕会刺痛朝廷和北洋的内心,也会让洋人顾忌,如果让洋人以为这是第二次北伐开始,事情恐怕就不会那么简单了,不单单是华军与几十万北洋军的战斗,很可能引发国际局势的变动。
由于长江以北的湖北省处于“双方共管”的奇特状态,因此在这里出现华国官方的人、甚至少量军队都不会引起震动,但一旦进入中原腹地的河南,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梁敦彦提出华国可以在河南和湖北的交界处设立中转点,但张康仁认为那里离灾区太远,灾民根本不可能跋涉这么远的距离,恐怕在路上都死光了。反复考量,最终中转点被设置在河南信阳,这里地处河南南部,不至于太敏感,又可以让灾民看到希望。
为了保证中转点的安全,张康仁提出华军派出一个师的部队负责保卫工作,当即遭到梁敦彦拒绝。一个华军师进入河南,一旦出事,北洋军得拿出一个军、三个师的部队对抗,那可是北洋近三分之一的部队。
按照华军实战的表现和北洋军自身会操的结果,包括段祺瑞等高级将领都一致认为,华军一个师可以抵挡北洋军三个师的进攻并不落下风。三个华军师的部队组成的进攻力量需要北洋军全军压上才能抵挡,两个军的华军部队组成的进攻力量,北洋军只有举手投降这条道路可以选择。当然,这是在比较乐观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所以,最终只有一个步兵团的部队被允许进入信阳守护中转点的安全,双方达成一致后,早已准备好的华国救援队伍立刻出发,并在半个月内大大缓解了河南的灾情,至少使因为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
对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