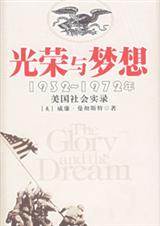光荣的荆棘路_林丹环-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每篇文章,都是读了一本或是几本厚厚的巨著以后才下笔。很多读者感言,不管题目有多大,读来却如流水般的轻松流畅,深入浅出,让人爱读,给人启发。去年1月2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百岁老人周有光答客问》的文章。文中,周有光说有新的考证“已经证明了”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人,语出惊人,引来明史学界的一番热论。最后学者陈梧桐站出来申明,目前一些认定朱元璋是回族的论说都是站不住脚的。记者采访的前天,周有光才从亲戚处得知自己这句错话引起网上一些网民的痛骂。“我患青光眼。医生说不要看电脑屏幕,就一直不知道这场风波。”他跟记者解释这是他看国外的资料得到的片面观点,他轻信了。为此他请亲戚在网络上申明“感谢骂我的人,纠正我的错误”,还把他的道歉和感谢言语打印成字条交给记者,嘱托记者把这段加入文中。人老心不老,也更重在其抛砖引玉之举。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年纪大了的缘故,周有光说和写的多是“狗屁不通”的杂文。因为写学术论文需要到图书馆去查书,很不方便,索性省了这道关,只写些杂文。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内容不止于语文问题,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百岁时,他把自己90岁—100岁之间的文章编成《百岁新稿》,2005年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笔耕不辍,勤于求新。
周有光讲其本行,也有声有色。在其百岁时的一次演讲上,他用诗句串讲古代岩画里的文字意思,让听众记忆犹新。外国古代有一个女子写情书,以画代字。她画了几条线,那是代表路,画了几个圈代表湖海,三角形的则代表房子。那意思是说,“熊妹问狗哥,狗哥几时闲?”为什么是熊妹呢?这个女孩的部落是拿熊做图腾的,也可以说她是姓熊;狗哥是表明那个男孩部落的图腾是狗,也可以说那个男孩是姓狗的。熊妹写信给狗哥,问他什么时候有空。“我家三姐妹,妹屋在西边。”我们三姐妹的房子,我的在西边,你来的时候不要走错了。“推窗见大湖,招手唤孤帆。”里面画一只手,表示招呼他来。“小径可通幽,勿误两相欢。”
“别人说我是‘新潮老头’,因为我主张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我比较早地提倡在电脑上写文章,不要爬格子。如今我在电脑上写了十几个年头了。”1988年4月,周有光83岁时,他有了一台中英文文字处理机。从此,周有光便用它写文章、写信。高龄“换笔”之后,他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入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自己用电脑用溜了,就开始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新潮”。
他们家的保姆不过30多岁,周有光老劝她学学电脑,保姆说:“我都老了,还学什么电脑呀?”周有光说:“我还没说老呢!我老伴86岁不也学电脑吗?”周有光不但说服保姆学电脑,还教保姆的女儿学电脑。假期里,保姆的女儿来到周有光家里,看到电脑高兴地说:“我们学校也有电脑,但是没有机会碰,只能远远地看。”周有光非常喜欢爱学习的小朋友,短短几天时间,就教会了她用电脑。
周有光还用自己的小破电脑帮忙恢复了一本“发行量最小、办刊人年龄最高”的刊物《水》,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杂志,由教育家张冀牖的儿女们自撰、自编、自印、自发,被著名出版家范用评价为“本世纪一大奇迹”,刊载的多是张家四姐妹及其夫婿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等文化圈名人家长里短的事、三姑六婆间的音讯通问。《水》1930年创刊,后因为四姐妹先后成家,加上战乱频仍,在印了25期后被迫停刊。60多年过去,1996年周有光用现代化的机器教86岁的妻子张允和学习汉语拼音和电脑打字,《水》也就被张允和敲着键盘恢复起来了。
周有光自称患“多语症”。他的挚友聂绀弩曾写了首打油诗赠他。诗日:“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去年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周有光眉飞色舞地讲自己,也“八卦”沈从文。主持人还时不时帮助他找口袋里的手绢擦唾沫横飞的嘴。周有光娶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沈从文娶了张家三小姐张兆和。沈从文追求自己的学生张兆和是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其传播广泛肯定也少不了周有光的大嘴巴。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著名学府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和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做媒的事,我也愿意。
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周有光讲到这一段,仍忍不住哈哈大笑:“胡适比我还‘新潮’呢。”
除讲自己家庭中的“八卦”外,周有光也爱讲讲邻居的“秘闻”。“七七事变”后,周有光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转移到四川,在重庆、成都等地工作。在重庆郊外的江安小镇,他和吴祖光成了邻居,常来常往,周有光开始爆料曹禺、老舍等人。曹禺最爱看书,夫人最爱干净,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大文人无奈,坐进澡盆,一手拿书看,一手划着水,用哗哗的声音佯作洗澡骗骗夫人。老舍最爱讲故事,一讲就离不开乌龟,大家说别讲了,换唱戏吧,结果他唱了一段《钓金龟》!
周有光不但爱讲“八卦”,且“八卦”语言幽默。某年,全国政协请委员们看戏,他带了只象牙望远镜,不时地拉近与舞台上的男男女女的距离,逗得邻座眼馋,三番五次借观。中场休息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的邻座,看把戏似的。他问朋友,你们看的是谁。朋友说是溥仪。周有光听了,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早知道他是皇上,我就进贡给他了。”
打趣总是礼尚往来,周有光也被丁聪取笑过一次。张允和喜欢听昆曲、评弹,正与夫君同好。遇有精彩演出,他们总是早早地来到剧场,正襟危坐。近年来,北京交通越来越拥挤,出门听戏已经不大方便,于是周有光老两口在平均年龄81岁的时候,商量着买一辆新式的残疾人用的三轮车。丁聪听闻此讯,赶忙为两人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周有光“驾驶”着一辆精巧的三轮车,张允和手持横笛坐在车上,老两口怡然自得。
也有周有光不常讲的“八卦秘闻”,被他隐藏了50多年之久。
1947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朋友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何廉,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周有光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聊天的内容,按他的话讲,“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周有光的外甥感叹,“中国有多少人见过爱因斯坦,又有几个人与爱因斯坦作过面对面的交谈?这应该是家中的头号新闻。但直到舅舅百岁华诞要制作一本贺册,我们与舅舅聊天时,才获悉此事”。
这位现年101岁的老人也有他的寂寞。年纪大了,别人请他吃大餐吃不动了;出门走远了,就需要轮椅,不能外出旅游。在家没客人来访,看书又看累了时,他就会看窗外的那棵大树。“树上有很多鸟,大鸟、中鸟、小鸟都有,天热的时候它们是中午来,现在开春了是早上来;对面那栋楼有个门洞,和我这个窗正对着,这很好,我从这个门洞就能看到街上的车、人;书架上还有这面镜子,透过镜子我能看到反方向的那栋楼。我的生活太简单了,我的天空就是半个书房。”
作者简介
李樱,杂志撰稿人,撰写的《新潮老头》颇有特色,受人关注。
【心香一瓣】
真正的衰老,不是容颜的衰老和身体器官的退化,而是心灵的衰老。有的人虽年纪轻轻,却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早生华发,已经未老先衰;有的人虽已至耄耋之年,却耳聪目明、思想清新、乐天知命。
周有光就是这样一位人老心不老的老人。他勇于求新,敢于承认错误,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乐观幽默,淡泊名利。通过作者的笔,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可爱”的老学者。
年轻人更当有这样一颗年轻的心,让心灵的天线接收乐观积极的信号,那么青春就会永驻。
。。c o mt。xt。小。说。天。堂
第3章 大师的眼睛
摩罗
一个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深深伤害过的人可以当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而不可能成为作家,因为即使一位平庸的作家也是由造化的捉弄和折磨造就的,一位伟大作家的诞生则几乎非得以心灵的巨大伤害和严重残缺为代价不可。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世界上最能抓住读者眼睛的眼睛,无疑是卡夫卡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充分宣示了他内心的柔弱和恐惧。也许你会像触电一般被他唤醒了自己内心同样的柔弱与恐惧,也许你内心苏醒的是对于一个柔弱而又恐惧的孩子的深深的怜悯与关爱。总之,只要你看见了这样的眼睛,你就一辈子摆脱不了他对你的倾诉与吁请。
卡夫卡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这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一生都害怕父亲,好像被他的父亲所压垮。其实他是被存在本身所压垮。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存在,他被存在的真相压得喘不过气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再合适不过。
刘青汉说,鲁迅笔下的狂人突然发现罪恶的人类“原来如此”,耶稣却知道罪恶的人类“本来如此”。这个精辟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中西精神文化的差异。可是,西方人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耶稣的结论,每一代精神巨人都是重新发现“本来如此”的。在他意识到“本来如此”之前,也惊恐地品尝过“原来如此”的震撼。
卡夫卡的眼神就是这种发现的惊讶与恐惧。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只是他随手记录下来的噩梦,他甚至立下遗嘱让朋友把这些文字全部烧掉。他实在不喜欢他所体验到的存在的柔弱、恐惧与痛苦,他深知“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他每天都在吁请信仰的降临,因为真正的生活就是信仰本身。
这是一双最真诚地为信仰而焦虑的眼睛。他好像决心把上帝看个清清楚楚,最后他说“上帝居住在神秘和黑暗之中”。
当我们相信神秘和黑暗之中居住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恐惧呢?
普鲁斯特的眼睛——梦幻
梦不仅是大脑的一种思维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而文学就是人类的梦幻。所以,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无法与梦脱尽干系。
世界上有一种病人,医生永远看不到患者的临床表现,因为这种病只发生在夜间。谁见过梦游者的身影和眼神呢?可是,自从普鲁斯特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每个有机会看到他的照片的人都可以见识梦游者的眼神和灵魂。
卡夫卡说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噩梦,这等于说人生就是一场噩梦。
普鲁斯特好像有不同的看法,他拉着卡夫卡的手,带他来到一座花园楼房,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的那张床上,恍恍惚惚地回忆起睡觉前母亲慈爱地拥抱他的温暖感觉。这时奶奶送来了一块馅饼,普鲁斯特还没有品尝就感觉到了浓郁的甘甜和馨香,这是对曾经有过的甘甜和馨香的回忆呢,还是在梦中幻想着的甘甜和馨香?
普鲁斯特依然拉着卡夫卡的手,迷迷糊糊地来到海边,欣赏阳光在海浪上跳舞,美丽的舞裙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金色。这时一个送牛奶的村姑款款走来,阳光在她脸上开成了一朵变化不拘的小花。普鲁斯特痴迷地赞叹,生活就像阳光一样,在任何地方都闪烁着诗意,诗人不过是这些诗意的感受器。
谁都知道,普鲁斯特因病不能接触阳光,只能长期封闭在室内。
他是一位生活的囚徒,这才是真正的囚徒。
卡夫卡禁不住嘟囔着说,可怜的梦游者,你都几十年没有见过阳光了。
普鲁斯特说,我生活中没有阳光,不见得梦中也没有阳光。生活不过是梦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噩梦又是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何必被那一小部分压垮呢?
一位诗人说,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就只是在这里。普鲁斯特说,不要以为我活在生活中,就只是在生活中。
人类是一个病入膏盲的梦游者,作家是唤醒梦中记忆的通灵师。
文学大师的存在方式就像村姑脸上的阳光之花一样变化不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疑惑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一只眼睛,从额头到下巴整个脸部就是他的眼睛。额头则是他的眼珠子。深重的苦难在这只眼睛里阴暗地闪烁,严重得无以复加的神经质在这只眼珠子上翻滚战栗。在他年仅24岁的时候,别林斯基就从这位《穷人》作者神经质的敏感与善良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希望,但是这颗希望之星升起得艰难而又缓慢。因为他要等着西伯利亚的十年流放生活给他以决定性的锻造。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令人惊奇的是,他体验苦难的深度,就是体验爱的深度。别尔嘉耶夫不无骄傲地说,俄罗斯作家常常因为爱而发疯。安德烈耶夫、迦尔洵都是这样的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加博大的疯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大师作比较的时候说:
“普希金具有除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特质和天才——他对全世界都抱有悲悯的同情心。”其实,普希金只是这一特质的开启者,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托尔斯泰身上。这一特质才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丰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明晰而又确定。他先是因为主张西方化而被流放十年,后来又因为强调俄罗斯民族本土传统而遭受文化界的攻击。他在精神上却更多地表现出犹豫、疑惑、徘徊、质疑等不确定的禀赋。他对赌博的痴迷和对癫痫病的眷恋说明他对一切未知事物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他不但热心展现底层人的苦难生活,同时也是最热衷描写圣徒精神的作家,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一位圣徒。可是他是唯一一个同时把对于上帝的疑惑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圣徒,他的极度神经质的敏感使他始终处于疑惑的状态。这些疑惑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弱点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