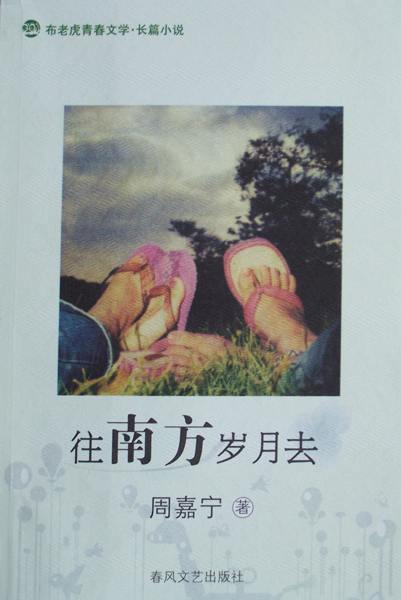南方周末至后台+第一辑-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有决定要写此稿。在这些日子里,我和编辑杨瑞春讨论最多的是这个稿子可能涉及到的各种新闻伦理问题。我们达成的一致想法是,尽管这个女教师家人的遭际是反映农村问题的既极端又充满多种共性的样本,但如果这个稿子对她的家庭产生了什么后果,也应该是我们能控制与帮助的范围内的,如果这种后果超出了我们控制范围内的,那还是不发为宜。
2月初的这些天,主要就是关于新闻伦理的考虑天天使我在焦虑中度过而无法动笔。在这些天,我也依然与这位女教师保持着联系,时时刻刻地关注着这个家庭这个村庄的一些变化。她也知道了我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于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的大意是说为了让社会了解像她那样的家庭与农村教师,我们应该写下来。她还说她不怕,如果真因此丢了教师工作,她也还是想当老师,哪怕去西部支教。正是她的这些话,使我有了写下去的决心。
四
这篇稿子最后被通过了,我的述评却因种种客观原因无法发表。这篇述评主要是从这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来观察乡村伦理资源被透支的情况、以及大学高收费与乡村贫困的紧张关系、农民抗风险能力弱和致富途径缺乏的关系,后税时代乡村基层公共财政薄弱与教师待遇的关系。这其实是能够表明主稿的价值取向与观察视角的评论,编辑杨瑞春对此也很满意。此文后来发在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记者手记专栏上。
在写那篇述评前,我本是想请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来发表看法的,但他说对此事他没有足够调查所以不发表看法,但他告诉我们,看了我的文章心里在滴血。我当然知道,如果是一个是象温先生那样的读者,他是会明白我在主稿里真正要表达与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也会从这样的信息里思考更完善的建设性意见。但普通读者在一个充满着如此多冲突与矛盾的事件面前,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评论是很容易误读的。
所以,我给关心此稿的一位好朋友发了短信,说:“没有这篇评论,我预感到稿子发出来后一定会有一场不小的风波,一场被误读的风波,甚至可能是诋毁南周的风波。”他说我过虑了,我说我有这种直觉。
五
这篇文章报道发表后,果然有了一轮如我所料的社会关注与风波。
对于那些善意的比较,例如所谓的“南周知音化”,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因为南周在这样的文本里所要传递的信息与《知音》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各种恶意的攻击,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作出回应的。
我只想在太阳下埋头工作,让汗顺着眉尖流下,让眼睛看到阳光与阴影,让心稳稳地贴于大地……
六
但对于正常的业务批评,我是乐于参与讨论的。
我想,这篇稿子遇到的最大的困扰是,因为涉及当事人太多的隐私以及若干敏感的地方利益,使不少方面无法用真实具体的名字。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新闻语境下,如何在保证新闻要素和保护当事人隐私间达上达到两全呢?如何在遵守新闻伦理与满足读者对真实感的追求上达致完满呢?如何在坚守新闻理念与保障政治安全间找到平衡呢?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想明白,也想请教诸位同仁。
另外,正如邓科老师所指出的,这个报道在描述这个女教师的性格冲突上还存在不足。这种心理冲突主要表现在“平时是天使(乡村教师),周末是魔鬼(卖身供学)”,我还没有细致地描述出来。我想,从记录这个时代的受苦者的心灵史的角度看,这种调查是必要的。其实,当许多宏大叙事碰到这样的心灵史时,一下子就会变得苍白与空洞。但我还没有很好地记录下来。
在调查时间上,我也觉得不够,在五天多采访中,有两天多被耗在与官员的周旋中,所以实际采访女教师卖身供学的时间太少。如果有更多的采访时间,就可以寻找更丰富的材料,也可能因此找到更令人信服的表述方式。但不能不说的是,这篇稿子正如前面已谈到过的,因为涉及诸多新闻伦理的问题,还有中国政治语境下一些的困境,所以当时并没有一定要做的决心。如果在上版前再作一番补充调查,也许可以使稿子做得更扎实更有力量。
2、杨瑞春:模糊的伤口
在记者傅剑锋贴出文章,公开回应对于《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这篇报道(下称徐萍报道)真实性的指责之后,类似声音从此销声匿迹。但对于这篇报道的一些遗憾,作为操作者,无论是从记者到编辑,我们从未讳言。尽管它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
在徐萍报道的采编过程中,我们面临了一些困境,稿件最终的呈现,是这些困境下的一个妥协方案。但我们今天以这种方式探讨它,就是因为这篇报道所面临的困境绝不只是某一篇报道的困境,这些困扰可能所有同道中人都会面对:在类似敏感题材的新闻操作和处理上,保护当事人和寻求真实性如何统一;如何解决坚持新闻原则和新闻把关制度的冲突:写作上记者如何取得表述的创新与突破,等等。
因此,徐萍报道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新闻艰难操作的一个样本。正如徐萍报道本身,假如你们只是看到一个女教师周末卖淫以供弟弟上学的悲惨故事,那么,我们很遗憾,我们本来是想给你更多,我们本来想让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伤口。
我们选择,我们承担
2月22日,做版,我盯着屏幕出神。电脑技术的方便,可以让我按下一个“替换”的命令,就把6000多字的文章中,女教师本来很有特点的名字便全部覆盖,而换为那个后来众人皆知的名字“徐萍”。我是仅有的几个人,看到过这篇稿子以真实人名和地点出现的原貌。那感觉完全不同。
“徐萍”,一个我临时起的,故意毫无个性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让有过屈辱经历的女教师隐藏在茫茫的人海中无迹可循,不受打扰,这让人安慰。
但在隐去了所有的,从核心人物到次要人物的真实姓名,甚至隐去了故事发生所在省份之后,这还是一篇新闻吗?在我的新闻从业经历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报道只剩下了一个影子。正如报道的配图:头版,主人公有个靠窗的一个侧剪影,数码照片本来有更多的面部细节,我们调大了照片的反差,让那些细节隐于黑暗之中。2版,背影,女教师在她自己的宿舍里坐在床上。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画面里有块写满了英语单词的小黑板,这对她的英语教师的身份是一种说明,或者说,我希望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用照片的直观可信弥补文章真实性的遗憾。但后来傅剑锋在看到报纸后,专门向我抱怨这张照片选得不妥,因为那块小黑板和墙上贴的观音像等细节透漏了太多的东西,对徐萍的隐私保护不利。
对徐萍的报道,一开始关键点是确认其真实性的问题,因为是徐萍主动和《南方周末》联系,我们对这件太过惊人的事情是否可信充满怀疑。从她和我们联系到记者真正出发去调查中间为时几周,徐萍几次和实习生马小六说到因为被拖欠工资,她的贫困已经让她不能承受。马小六询问我是不是应该先给她寄点钱的时候,我的态度却还是要谨慎——说起来真是有些“冷血”。一直到傅剑锋和马小六出发,我给了200块钱给马小六,还叮嘱他确认情况属实再给徐萍,要是假的就给我拿回来。
但当记者见到徐萍,并且发现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之后,报道的主要矛盾就转变为如何既报道徐萍又保护其隐私的问题。傅剑锋对这个问题疑虑重重,特别是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女大学生卖淫的报道出了麻烦之后,他多次打电话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的建议是让他充分和徐萍本人沟通,在这个问题上尊重她的意见。
因为当时我们的介入,徐萍等教师被拖欠的工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们的想法是,不能报道出来固然是损失,但至少这次采访会解决一些弱势人群的生活问题,也算没有白去。
徐萍是个本性单纯的女孩,她开始一点都不为会被认出来担心,因为她所在的这个小地方平常根本看不到《南方周末》。但傅剑锋当时甚至忧虑,即使和她讲了公开报道有可能带来的损害,有可能对她依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她对于一篇《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所带来的影响还是没有准确概念。但后来给傅剑锋触动的是,她的决心很大,希望媒体能够关注像她这样的人的命运,即使付出被人认出的代价。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徐萍的这个做法,倒是让我觉得作为佛教徒的她确实有大乘佛教的精神,因为之前碰到的许多爆料者,大多更为关心自己的利害(当然也无可厚非)。
所以在其后,我们一直希望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在这个点上,真实性和隐蔽性的结合能够达到最好。但正如在照片问题上显示的,事实上这个尺度很难把握。我不认为现在连省份都隐去的方式是最好的,但什么是最好的,我其实也不知道。
做记者做编辑做到一定程度总会面临一些新闻伦理方面的困惑,并且逼迫你必须要作出一个选择,也许你伤害到一个人,但报道会推动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此时如何选择?一些新闻学教材里提出很多类似的案例,并且给出一个是非的评判。但我觉得有些是非是很难按斤两计算的,我只能说这次非常幸运,我们没有被逼迫做出最坏的选择。
回想起来,不论是从记者到编辑还是最高层,我们一直把徐萍安稳生活的权利置于报社利益之前,我对此深感自豪。即使我们因此遭遇过某种程度的质疑,但与因伤害了一个人而怀有的负疚感相比,我们宁愿承担质疑。
当然,这是对新闻标准的一个挑战,一篇报道的基本要素可以退到何处才是边界?我想我们是做了一次尝试,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
《南方周末》的加法和减法
在讨论徐萍报道的这期评报会上,我问新闻部的同事,你们认为这个题材适合上头条吗?没有人反对,而且有人非常鲜明地支持说当然应该上——但事实上,在我们北京站的评报中,有人曾经提出这一题材是否应该拿到头条来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南方周末》的业务讨论气氛非常自由,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传统之一。
所谓头条问题,内涵应该是《南方周末》的方向问题,也就是《南方周末》的选择标准的问题。以徐萍上头条,反对者主要的想法可能是认为“卖*”题材严肃性不足而猎奇色彩有余。
在徐萍这样一个色彩复杂的题材上面,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我在内部评报会上说到一个观点,“没有猎奇的题材,只有猎奇的操作”。讨论类似的问题就好比在讨论是否应该将《茶花女》或者《羊脂球》称为严肃文学。
我们是否在徐萍这个事情上,真的可以了解什么叫“生活比文学更为荒诞”,正因为事实本身的不可思议,我们比其他题材更强调其庄重性和严肃性。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希望这是一条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报道,我们希望呈现在这个女教师身上的一种朴素的人性的光辉。
但是还不止于此,我们不能只能告诉读者一个故事就结束。梅尔文?门彻在他的著名的新闻学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文版中说,“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应懂得把事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思考,来发现其原因和结果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记者不禁要不断发展采访报道的技巧,还要扩展对人的理解,对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徐萍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个置身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文化中的女教师。我们希望通过徐萍,来探讨关于中国农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在很多时候,评判新闻的高下,其实是在评判一种价值判断的能力。优秀的报道应该能够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优秀的报道应该赋予事件以意义。我们在操作徐萍稿件的时候,一直清醒地在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的框架中,解决这一问题的纵深稿非常重要。这就是那篇未能刊发的纵深稿《不让姐姐再流泪》,具体观点不在此赘述。承载这些功能的部分,我曾经考虑由专家对徐萍的事情发表评论,但后来还是决定让傅剑锋以记者手记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傅剑锋对于这类问题一直有所积累,而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有所集中,有所发散的评论,希望重要的是点出问题,启发读者思考。
傅剑锋拿出来这篇稿子之后,我甚至比对他写的主稿还要满意。这两篇稿件的搭配使整组报道的分量都大大加重。很可惜,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最后没有出来,而这一重要的缺失确实对于读者理解我们的意图产生了困扰。因此,只是报纸呈现的部分,让读者产生对于南周在追求猎奇效果的印象,其实并不奇怪。
事实上,在使用材料方面,因为徐萍对于记者的彻底敞开心扉,关于徐萍和她的家庭,如果追求猎奇,记者拿到太多的材料可以去吸引眼球。如果是一家小报,那么这些内容将会是填充版面的最精彩内容。但是,我们最终舍弃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与我们要表达的主旨无关。
我想说,在做这些加法和减法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南方周末》式的。正义、理性、良知、爱心”,是这份报纸的精神核心。
记者的宿命
美国有个普利策新闻奖被取消的案例,《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库克一篇关于8岁吸毒男孩的报道,被证明纯属伪造,当时那位记者提出因为保护被采访人的缘故,不能使用真实姓名。
我一定比那篇报道的编辑要轻松得多,因为通过对记者采访过程的密切跟踪,我知道真实性不是我们报道的问题。但在采访和呈现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提高。
同样是没有名字的报道,我相信反而是普利策奖那篇伪造的报道看起来更加天衣无缝,它要赢得那么多苛刻评委的心,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打动人的细节。
需要说明的是,徐萍文章中有些让人生疑的地方,事实上是后期的一些不当的处理导致,但我们讲故事的技巧确实还带有一定遗憾。
特别是报道对徐萍的行为逻辑的探讨和性格塑造方面,感觉不够充实。傅剑锋非常诚恳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些后悔,应该再回去一次,进行更为扎实的采访。但同时他表示苦恼,因为这个题材的特殊性,一些问题他感觉到很难问出口。比如说,到徐萍家里做采访时,徐萍提出来她不希望记者过多和弟弟们谈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大弟弟,别的弟弟根本不知道徐萍的经历。大弟弟也知道得不多,他们平常很忌讳谈及这个话题。这个要求说起来无可厚非,但对傅剑锋来说,他无疑是在放弃了能够拿到更多细节,从而增加文章可信度的机会。
有一个说法,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对事件“冷静而又充满关切”。但事实上,需要冷静到什么程度?关切到什么程度呢?《南方周末》上海站的记者朱红军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在他去调查一家民营慈善医院的时候,对院长本身的动机产生怀疑,在第一次采访之后,他“赶着准备了十余个自以为极其犀利的问题”,“我的设想是,把他问的拍起桌子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结果,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会见客人,他们只好在隔壁房间等。十分钟后,隔壁传来“院长昏倒了”的叫喊。他们出得门去,看到老院长已经被众人围着,躺在了沙发上。老院长在一帮人的手忙